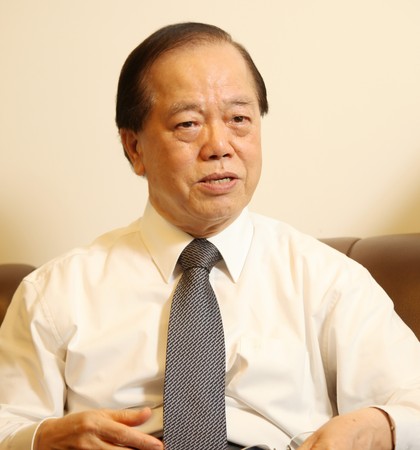苏友辰/【谢明达案检提非常上诉】最高院检火线交锋为哪桩
▲最高法院身为终审法院,不自为终局裁判,反复发回只是让当事人受尽诉讼折磨,正义迟延。(图/记者季相儒摄)
前台北市议员谢明达被控在1998年担任市议员期间,利用质询及调阅资料手段向捷运局施压乔人事,收贿220万元,一审到高院更三审皆判有罪。争讼18年后,最高法院于2018年8月间,以难以认定有对价关系等理由,罕见地自为改判无罪。当时引发舆论热议,连司法院内网「法官论坛」也有不少批判声浪;检察总长江惠民甚至为此提起非常上诉,认为最高法院自行认定事实,且未对争议之处进行言词辩论即自为判决,已违背法令,难昭信服。
2018年12月15日,最高检察署吴巡龙检察官即以「谢明达案应送大法庭」为题投书媒体提出批判。近日,最高检察署为因应最高法院言词辩论常态化及大法庭制化,于2月26日成立诉讼组,并拟就谢明达案最高法院无权自为无罪判决,以及是否应经言词辩论等主张,声请最高法院开庭辩论,引起该案受命法官黄瑞华于2月20日发表「三审法官致检察总长公开信」叫阵对抗。该文痛切指出,终审法院不自为终局裁判,反复发回,使当事人受尽诉讼折磨,法院积案如山,资源浪费,正义迟延,人民、同仁及司法公信三输云云,赢得社会大众的喝采!
不特此也,黄法官文中援引该院迄今至少有7件撤销高院有罪及自判无罪的判决先例,认为前此并无发生争执,何以突然对谢明达案提起非常上诉提出质问;隔天,吴检察官再度投书公开回复最高法院黄法官的置疑。从院、检一来一往在媒体笔战交锋看来,就双方争执的问题,或许可以从非常上诉分高下,如果未能从此定纷止争,检方扬言还要求助于未来新设的「大法庭」作出统一见解,以平息争议。
探讨此项司法重大的争议,其症结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94条第1项前段规定,即第三审法院应以第二审判决所确认之「事实」为判决基础,以及第398条第1款规定,即第三审法院因原审判决虽系违背法令,而不影响于「事实」之确定,可据以为裁判而撤销之者,应就该案件自为判决。究竟该两条所指「事实」是否囿限为「犯罪事实」,院检各自解读适用,似各有所本,一时是非难辨。
依笔者浅见,最高法院自为判决的确定事实,即关说乔人事与收受200万元的情节并未改变,只是两者之间有无对价关系价值判断不同而已。最高法院依照职权调查及事实审证据诉讼资料,本于法律确信,认定无对价关系而改判无罪,当无违背法令之可言。
▲前北市议员谢明达涉贪案,去年最高法院自为无罪判决,引发院检对于最高法院是否可自为判决的笔战交锋。(图/记者吴铭峰摄)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刑事诉讼法》第398条第1款所谓「不影响于事实之确定,可据以为裁判者」,于个案的适用上应如何判断?其实,这把解套的钥匙早在2012年1月,司法院成立的刑事诉讼法研究修正委员会所拟具的草案已作了新的规范,以避免认定之争议及案件无谓延宕。
依照草案现行第398条第1款规定已被解构,移列至第401条第1项但书:「但第三审法院认依其调查所得诉讼资料及原审法院或原第一审法院调查之证据,可据以为裁判者,得就该案件自为判决。」此新的规范即跳脱现行第394条第1项前段及第398条第1款含义不明的框架,只要最高法院依同法第393条但书进行职权调查结果,以及审酌原审法院或原第一审法院调查的证据,当可以就最终事实是否犯罪该当或行为不罚情形审查确认,进而就该案件自为判决,于法自属有据,此项犯罪事实之改变纷争当可据以解套而落幕。
至于,检方批评谢明达案最高法院未对争议之处进行言词辩论,是否违反正当程序而违背法令?依《刑事诉讼法》第389条第1项规定:「第三审法院之判决,不经言词辩论为之。但法院认为有必要者,得命辩论。」此一条文给予最高法院法官于个案中决定是否开庭的裁量空间,但结果却是实务上我国历年来开庭辩论次数寥寥可数,问题即在于所谓「有必要者」,如何解释适用?
对此,国内《刑事诉讼法》学者陈运财教授曾为文提到,作为终审法院之判决应否经开庭辩论,参照美国、日本等立法例,就运作模式而言存在下述几个做法:
1.原则重要性模式,指当事人所为之上诉主张涉及法律见解具有原则上的重要性者。
2.撤销必要性模式,是指终审法院于认为当事人上诉有理由而有撤销原判决之必要时。
3.重大案件模式,例如针对死刑案件,不论当事人上诉有无理由,亦不论其主张是否涉及法律原则的重要性,一律开庭辩论。
陈教授更进一步建议,在现行《刑事诉讼法》就第三审上诉审采取所谓事后法律审查的结构,以及上诉目的以统一法令之解释为主的考量下,以第一种的原则重要性模式较为可采,此项看法也符合我国未来建造金字塔型第三审为「严格法律审兼采许可上诉」的诉讼架构规划(草案第377条之1)。而司法院长许宗力甫上任时,对于「最高法院就重大法律争议案件应常态化开庭辩论」的政策宣示,也与法务部达成共识。若以此衡量谢明达案,最高法院未经言词辩论即自为判决,似有欠周延考量。
为杜绝争议,我国应订立标准或亦可兼采不同模式,作明确规范修法,让实务有所遵循,较为妥适;而前开新版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目前司法院已送请行政院会衔中,如能加快脚步,尽速送请立法院审查,赶在本届完成立法,院、检两方应可各自鸣鼓收兵,循此正道理性处理,以民为本,以人权保障为念,莫让正义迟延而变调,司法改革当可更往前迈进,人民幸甚,国家幸甚!
好文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