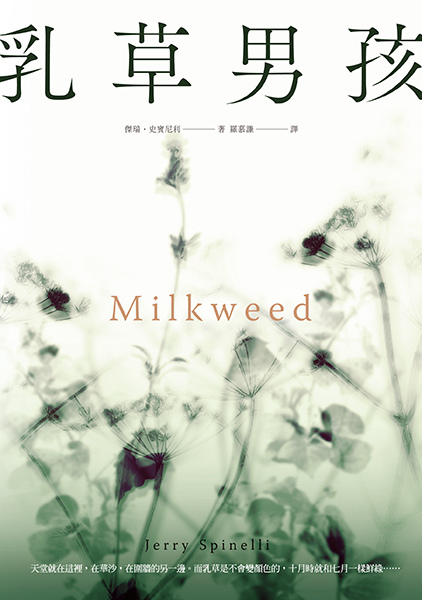【文学新象】乳草男孩(Milkweed)[精彩内文试读]
15 秋
人们在离去。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多人在街上走。我们站在一个街角观看。
他们都是犹太人。我看他们手臂上的臂章就知道了。每个犹太人都要戴一个白底蓝星的臂章。这样一看就知道谁是犹太人,因为现在不是每个犹太人都留胡子。在此之前,我只在这里看过几个犹太人、那里看过几个犹太人,从来不知道有这么多犹太人。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街道,但是他们全往同一个方向走去。小孩拉著小拉车,上面堆满玩具、锅子和书。大人拉著摇摇晃晃的大拉车,上面装满家具、衣服、图画和地毯。他们似乎把整间屋子的东西都清到大拉车、小推车及肩膀上鼓鼓的袋子里。大的拉车由马拉,小的拉车由人拉。马和人看起来都一样,缓慢吃力地前进,眼睛看著地面,被背上的负荷压得弯下腰。马没带臂章,但是牠们显然也是犹太族。
那是一个蓝白色的游行──和大黑靴壮观的游行多不同啊!如此缓慢,如此安静,几乎听不到有婴儿在哭。成千上百只大黑靴踏在地上的砰砰声,现在变成了破旧鞋子拖在地上的声音;坦克的隆隆声成了推车轮子的喀喀声。
我举起手遮住阳光。「他们要去哪里?」我问乌里。
「贫民窟。」乌里说。
「什么是贫民窟?」
「命不好的人住的地方。」
游行的人很安静,但是游行队伍后却有不少声音。吹口哨、欢呼及打破玻璃的声音。每次有犹太人从自己的房子走出来加入游行,立刻就有别人冲进去。有些院子里还有人在打架。人们从门口台阶上飞下来。顶楼的窗户被掀开,屋子的新主人在游行的人头上大喊:「这是我的房子!」
但是我对贫民窟这个地方更感兴趣,不论它在哪里。「宵禁之前回来。」是乌里给我的唯一警告。
我加入犹太人一起走。有一会儿,我走得得意忘形。自从看过大黑靴壮观的游行后,就希望自己也能加入游行。于是我跟著自己想像中的游行跨步前进,超越一个又一个慢步前进的犹太人,头抬得高高的,双手摆动,正步前进,仿佛我也穿著又高又亮的大黑靴。如果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那我一定没注意到。没有人说一句话。很快地,我的想像就幻灭了,脚步也缓下来,像其他人一样慢步前进。
我发现自己走在一个年纪看起来和乌里差不多的男孩旁边。那男孩背著一个鼓鼓的大灰袋,像是里面装了南瓜。
「你认识乌里吗?」我问。
那男孩不理我,只是瞪著前面看。
我提高声量又问一次:「你认识乌里吗?」
那男孩根本没注意到我的存在。但我不是这么轻易就可以打发。我决意继续跟他讲话。
「乌里的头发是红色的。他不是犹太人。」我总是很小心不泄漏乌里的身分。「我可以摸摸你的臂章吗?」他没回话。我伸手摸摸他的臂章。「我是吉普赛人。」我说,「也许有一天我也会有个臂章。」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条香肠。(只要我能找到香肠,我总是会随身带著它,然后有空就拿出来咬一口。)我把香肠伸给他,问:「你要咬一口我的香肠吗?」这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眼睛动。但是走在另一边的女士说:「他不饿,请你离开。」
真是不知感恩,我心想,但是我依她说的走开了。我从一个人走到下一个人身边,不停地问:「你要去贫民窟吗?……你在贫民窟会有个漂亮的房子吗?……到贫民窟还有多远?」但是没有一个人回答我。我请每个人都咬一口我的香肠,但是没有一个人要吃。没有人看到我,或者至少我是这么想──除了某些女士肩膀上的狐狸脸。牠们又黑又圆的小眼睛无止无尽地瞪著我看。
有一回,我看到一只身上有斑点的母马。「格雷塔!」我大叫,然后跑向牠。但牠只是在我头上流口水,于是我知道牠不可能是格雷塔。
我听到小孩们在唱歌,还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老人鹅!一!二!三!」
我跑过去。「柯查克医师!」我冲过去抱他,他被我撞得晃了晃,但是满脸笑容。「柯查克医师,你们也要去贫民窟吗?」
「是的。」他说,「我们全都要去。」
「贫民窟很漂亮吗?」我问。
他微笑,说:「我们会把它弄得很漂亮。」
我和孤儿一起行进。他们在唱歌。我不知道歌词,于是就跟著大声哼唱。我跟他们在一起时,自己也想当孤儿。在歌曲和歌曲间,我可以听到拉车和人们前进的喀哒喀哒声。一次,一栋房子的高窗户传下来一个声音:「孤儿派!」
然后我看到亚妮娜了。她步履沉重地跟著家人一起往前走。她肩膀上的袋子几乎要掉到地上了。我跑过去,大喊:「亚妮娜!」
她看著我,然后露出微笑。「米夏!」
我冲口就问:「你们也要去贫民窟吗?你们去哪里了?你们的房子里现在住著别人。我不喜欢他。他把啤酒倒到我头上,于是我把他的脚压碎了。」她大笑。我又说一遍。「我把他的脚压碎了!」她笑得更大声了。
「亚妮娜,」我说,「没有人看到我,只有柯查克医师看到我。」
一个声音说:「他们看得到你。」是走在我们后面的男人在说话。他拉著一辆东西堆得老高的拉车,用带子绑在肩膀上。他是我在生日派对上看到的其中一张脸。
「那是我爸爸。」亚妮娜说。
「他们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对亚妮娜的爸爸说。他身后的拉车喀哒喀哒作响。
「因为他们怕你。」他说。
我大笑,说:「世界上没有人怕我。」
亚妮娜瞪我一眼,说:「不要笑我爸爸。如果他说他们怕你,那他们就真的怕你。」
我抬头看他。他和其他人一样,只是瞪著前面看。他有一双大眼睛,栗子般的红褐色,和亚妮娜的眼睛一样。
「他们为什么怕我?」我问。
他还没回话,亚妮娜就尖声说:「因为你不是犹太人啊!不然你以为是为什么?」
我根本无法相信:有人会怕我。我掏出香肠,问亚妮娜:「要咬一口吗?」
「不行!」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但是太晚了。亚妮娜已经把香肠抓过去,咬了一大口。她把香肠拿给她爸爸,他看著香肠好一会儿,最后也咬了一口。他把香肠伸给那女士,但是那女士摇摇头。然后另外一只手伸过来把香肠抢过去,最后就被这人给吃完了。
「那是我叔叔什普瑟。」亚妮娜说,「他跟我们住在一起。」
我伸手过去抱住亚妮娜肩膀上的袋子,说:「让我来背。」
她把袋子交给我,然后就蹦蹦跳跳地往前跑了。我把袋子甩到肩头上,它重得简直要把我往后拉。「袋子里是什么啊?」我大声问亚妮娜。
亚妮娜蹦蹦跳跳地跑回来。「我最喜欢的东西。只有滑板车不在里面。妈妈不让我带滑板车。」她瞪著那女士看。
我指著她手臂上的臂章。「妳喜欢妳的臂章吗?」
「托比亚斯──」亚妮娜的妈妈说。
「没关系,」亚妮娜的爸爸说,「他是那个小男孩。」
「我知道,那个小偷。」
「没关系的。」
前面响起一阵喧闹。推车轮子的喀哒喀哒声更大了。「走……走……」亚妮娜的爸爸嘟哝,然后弯下腰更使劲地拉车,直到他上半身几乎与马路平行。游行的速度加快了。锅子掉在地上的声音像是悲惨的电车铃铛声。人们在喊叫。人们在跑。
16
「一个壁橱?」乌里问。
「一个壁橱。」我在泥土上用脚画出一条线,把我们的马厩分成两半。「就这么大。什普瑟叔叔就是这么说的,『我们住在一个壁橱里。』」
我正在向乌里叙述当天的经过。我告诉他如何遇到亚妮娜和她家人,还有大家如何冲进贫民窟里,还有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贫民窟一定是个很棒的地方。我告诉他我们如何走进一个大庭院,一个地上都是泥土的四方场地,四周是一栋栋房子又高又平的墙壁,还有亚妮娜的爸爸如何催促什普瑟叔叔──「赶快!赶快!」──于是什普瑟叔叔立刻冲进其中一栋房子,跑上楼,我和亚妮娜跟在后面,但是我最后才到,因为我背上的袋子太重了。然后什普瑟叔叔在四楼一间公寓的门口坐下来,我和亚妮娜也在旁边坐下来,直到亚妮娜的爸爸和妈妈吃力地爬上来。然后我们又下楼回到院子,把拉车里的东西搬到楼上,有些东西需要两到三个人一起抬,但总是有一个人留在四楼,坐著守住门口,而这栋房子是间「疯人院」──亚妮娜的妈妈就是这么说:「疯人院」──因为这么多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而整栋房子只有一个楼梯,而且每个门口都坐了一个人。
把所有的东西都搬上去后,亚妮娜的爸爸和什普瑟叔叔便用槌子和脚踢把拉车拆掉,然后把每块灰色的、裂开的拉车碎片都搬上楼,连轮子也不例外。最后所有的东西都搬到屋里、亚妮娜的爸爸关上门后,什普瑟叔叔便说:「我们住在一个壁橱里。」
我告诉乌里我离开时还发生了什么事。亚妮娜想和我一起到院子,但是她妈妈不准。于是她只跟我走到公寓门口外,然后她说:「等一下。」又走回屋里。出来时,她咧著嘴在笑。「闭上眼睛,把手伸出来。」我照做,然后感觉到手上有个东西。「把眼睛睁开。」
那是一块巧克力糖,奶油口味,里面夹著一块榛果。只不过它其实只剩一半,连里面的榛果也只剩一半。
「我咬了一口才发现它是榛果口味,」亚妮娜说,「然后我就为你把它留起来了。」
我把它吃掉。我已经好久没吃奶油榛果口味的巧克力糖了。我以为这辈子再也吃不到了。亚妮娜一直在笑。我跑下楼梯。
我又回到贫民窟时,被一道大墙挡住。人们正在用砖块筑一道墙。它有三个我这么高。我沿著墙走,一直走到一段尚未完成的地方,这里的墙只有几块砖那么高。我跨过去。有人在喊叫,我赶快跑。
要跑得快并不容易,因为这次我又背了一个大袋子。只不过这次袋子里满是食物。现在正是收成的季节,只要手快脚快,收获就会不错。
我找到他们的房子。它位在尼斯卡街。我爬上楼,走到门口,敲敲门。一个不耐烦的声音问:「谁啊?」
「米夏•皮苏斯基。」
我听到一声尖叫,然后开锁的声音。门开了,亚妮娜高举双手,大喊:「米夏!」
亚妮娜的妈妈躺在角落里的一个床垫上。她睁开一只眼睛,嘟哝著说:「又是你。」
「里面是什么?」亚妮娜指著袋子问。
什普瑟叔叔把门甩上,锁上锁。
「吃的。」我说。屋里中央有一张方桌子,我把袋子里的东西全倒在桌子上。
亚妮娜拍拍手。「吃的!」
白萝卜和苹果滚到桌上,然后又滚到地上。桌上有一把把的胡萝卜和芹菜、一条条的面包、一罐罐的果酱和糖浆及一袋袋的糖和一串串的香肠。每个人都站到桌旁,连亚妮娜的妈妈也从床垫上站起来。
「你从哪弄来这些东西的?」亚妮娜的爸爸问。
「各种不同的地方。」我说。
什普瑟叔叔把一条胡萝卜折成两半。「臭兮兮、手脚快的小偷。」
亚妮娜的妈妈打开一个满是粉尘的白色袋子。她把一根手指伸进去,然后用嘴巴尝一尝。「这是发粉,你要有烤箱才能烤东西。他在这里有看到烤箱吗?」她走回床垫,脸面向墙壁躺下。「我还记得烤箱是什么样,我曾经有一个。」──她咳嗽一下──「以前。我以前还是个人。」
什普瑟叔叔眼神悲伤地看著她。「以前。」
「外面有一道墙。」我说,「为什么外面有一道墙?」
「免得地痞流氓进来。」什普瑟叔叔冷笑著说。
「那你怎么进来的?」亚妮娜问我。
我告诉她我找到一段墙比较矮的地方,然后跨过来就是了。我说:「我什么地方都去得了。」我不是在吹牛,就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现在已经爱上我的小个子、我的速度和我的狡猾。有时我觉得自己像只小虫或小老鼠,可以钻进各种连人眼都看不到的地方。
有人在敲门,什普瑟叔叔立刻把手指放在嘴唇上。「不要说话,」他低声说,「我们不在。」但是亚妮娜的爸爸喊:「谁啊?」他也没辙了。
「赫蓝‧雷夫考维兹。」门外喊。
亚妮娜的爸爸去开门。「请进。」
赫蓝‧雷夫考维兹走进来时,什普瑟叔叔立刻丢了一件外套到桌子上,把食物都盖起来。赫蓝‧雷夫考维兹脱下帽子,拿出一张纸,说:「米格兰医师──」
亚妮娜的爸爸接过纸,说:「我不是医师。」他走到一个摆在地上、腰一般高、看起来像箱子的东西。他拉了一下,那东西便像翅膀一样打开。原来那是一个柜子,里面有好多小抽屉。两边的门内放了一排排的罐子,有些装著粉末,有些装著各种颜色的液体。它让我想起我们的理发店。我好奇这些瓶瓶罐罐怎么没在穿过城市的晃荡旅程中碎掉。
亚妮娜的爸爸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什么,装进小信封,然后交给那人。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苹果。他看起来快哭了。「我真希望──」
「走吧。」亚妮娜的爸爸边说边陪他走到门口。「不用了,走吧。」
那人转过身来碰了碰米格兰医师。「再见。」
「再见。」
什普瑟叔叔关上门,锁上锁。他对著亚妮娜的爸爸摆动一根手指。「明天这里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我们会被烦死。」
米格兰先生把翅膀推进去,柜子立刻又变回不起眼的箱子。「那你要我怎么办?全留著我们自己用?他拿著处方来,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
「一星期后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会把你搜刮光。」
「也许一星期后我们就离开这里了。」
「如果我们离开这里,那就是进我们的坟墓。」什普瑟叔叔指著窗外。「你以为牠们筑那道墙只打算用一个星期吗?要是我们真能离开这里,那真要算我们幸运了!」他大吼。
亚妮娜的妈妈在床垫上呻吟了一声。
亚妮娜和我躲在一个角落里。这个角落以后就会变成我们的角落。
「我爸爸是药师。」她告诉我。
「什么是药师?」我问。
「药师是做药的。」
「什么是药?」
她用奇怪的眼神看著我。「药能够让生病的人的病赶快好。像药丸、药油都是药。」她做了一个鬼脸。「恶。」
「你的爸爸叫托比亚斯‧米格兰。」我说。
她眉开眼笑。「对。」
「你叫亚妮娜‧米格兰。」
「对!」
「我是米夏•皮苏斯基!」
她拍拍手。「对!」
什普瑟叔叔瞪著我们看。亚妮娜对她吐了个舌头。我咯咯笑。现在我不只自己有一个姓,还知道别人的姓。我不停地咯咯笑,仿佛有人在搔我痒。
17
突然间,大家都跟著我和乌里住在马厩里。表情严酷的伊诺斯,爱开玩笑的库巴,往我脸上吐烟的费尔迪,只有一只手臂的欧拉克,没穿鞋的大亨利,不说话的灰脸琼恩。还有好几个似乎没有人认识的男孩。
「我们就跟紫色的大便一样显眼。」伊诺斯说。他说自从犹太人都搬去贫民窟后,他们就没办法再混在群众里。「而且到处都有告密的人。」
「什么是告密的人?」我问。
「就是告诉大黑靴,犹太人都躲在哪里的人。」
「我真高兴我不是犹太人。」我说。
他对著我冷笑。「别担心,贫民窟也是给你住的。我听说他们连吉普赛人也抓。还有残障的人。还有疯子。如果你想平安无事,当只蟑螂。」
我们附近一定有一个告密的人,因为一天早上,我们还睡在马厩阁楼上时,马厩的门突然被掀开,有人在大吼大叫。我们四处逃散──就跟蟑螂一样──但大黑靴到处都是。一个新来的男孩从马厩阁楼跳下去。他在半空中被枪射中,然后像个布娃娃般瘫到地上。
他们把我们带去贫民窟。自从他们把墙盖完后──墙顶上还铺满碎玻璃和有刺的铁丝──我就无法去探望亚妮娜。我将此视为对我个人的侮辱和挑战。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去哪个地方而被挡在外头,我深信很快就会找到到达墙另一边的方法。不过,我还是很感激我们的陪送者让我现在这么轻易就进入贫民窟。
路途上,有另外一件事盘据在我的心头:乌里。他没跟我们在一起。大黑靴突袭时,他不在马厩里。这并不稀奇。最近这几星期,乌里常常自己跑出去,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回来。凭著一头红发和「我属于这里」的隐形功力,乌里相信自己永远不会被当成是犹太人。他在街上毫不畏惧,而且他相信自己比大黑靴更聪明。
乌里要消失前,我总是会知道:他会把拳头顶在我的下巴下,然后从咬紧的牙齿间对我低声说:「不要让我听到……」他的意思是他已经指派几个男孩盯著我,免得我又去做什么特别笨和蠢的事。如果他知道我真的尽了我的所能听从他的警告,我想他还是会很吃惊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在的时候,我还更想当笨蛋和蠢蛋,他不在的时候我反而不敢。
我从来不觉得需要为乌里担心。我相信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处理。但是,现在边走边被大黑靴的步枪戳,我还真纳闷他的现况。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他回到马厩发现都没人,会怎么想?如果他找到我们,我也不会吃惊。我知道他一定会找到我们。
大黑靴没叫我们走人行道,而是走在马路中间。马车和汽车都让路给我们。行人在看我们。我们在游行!我心想。但是行人并没有安静地看我们的游行。
「你们这些臭小偷,再见!」
「到墙的另一边去吧!」
「臭犹太人!」
我根本无心跟他们说我不是犹太人。
在一条街上,我们沿著电车的铁轨前进,然后有辆电车朝著我们开来。我们犹豫了一下。大黑靴吼了几声,我们又继续前进。我们没停下来,但是电车停下来了。然后,伴著一阵当啷声,电车开始往后退。这就是我们走在这条街的情景:我们一行人往前行进,电车则在我们面前往后开。
很快我们就转进另外一条街,墙就在那里。左右两边,墙无止无尽向两边延伸。墙的砖是红色的,天空是亮蓝色的,有刺铁丝的结像女士的耳环闪闪发亮。一只黄色的鸟飞到铁丝的弯卷上,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又飞走了。
我们来到一座大门前。守卫把门打开,我们走过去。大黑靴留在后面,没跟进来,其中一个对我们深深鞠躬。我不知道他是在嘲笑我们,也对他鞠了一个躬。他嘲我屁股踢了一脚,让我飞趴到地上。大门砰地一声关上。
我径直飞奔到米格兰家的公寓。亚妮娜开门时,我大声宣告:「我现在也住在贫民窟!」
「正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什普瑟叔叔说,「又一个邻居。」
我没看到亚妮娜的爸爸和妈妈。「你爸爸妈妈呢?」
亚妮娜告诉我,她爸爸被带出贫民窟、带出城,去参加一个工作小队。她妈妈则在华沙一个工厂里为大黑靴士兵缝制服。只有有工作许可的人才能走出砖墙的大门。
「我们到外面吧!」我说。
我们从公寓冲出来,跑下楼。什普瑟叔叔在我们身后大喊:「戴妳的臂章!」
外面清冷明亮。我们像狗炼被放开的小狗在院子里到处乱窜。什普瑟叔叔的声音从窗口传下来,「妳的臂章!」
我们跑到街上去。「妳为什么不戴臂章呢?」我问亚妮娜。
「那你为什么不戴?」她问我。
「我不是犹太人。」
「嗯,我只是个小女孩。谁会管我这个小女孩?」她转著圈。「再说,我们现在住在贫民窟,很安全。」
我们沿著街道往前跑。
在我的眼里,墙的这一边和另一边看起来没什么不同:到处都是吵闹的人群。连趴在富有女士肩膀上的狐狸毛看起来都像是随时会开口讲话。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人在叫卖东西。
「镜子!镜子!完整的镜子!」
「漂亮的图画!三张算一张的钱!」
「玩具!玩具!」
「梳子!便宜的梳子!」
我看到一个只有一只手臂的男孩。「欧拉克!」我大喊,然后我们跑向他。欧拉克瞇著眼睛,用他唯一的一只手遮住阳光。「欧拉克只有一只手臂。」我对亚妮娜说。
亚妮娜打我一拳。「我看到了。」她转向欧拉克,说,「你的手怎么了?」
欧拉克低头看他的右肩膀。有一会儿,他似乎有些吃惊自己的右手臂不见了。他皱起眉头,最后说:「火车。」
亚妮娜向他伸出手。「不要难过。这只手还是好的。」
「这是亚妮娜‧米格兰。」我骄傲地宣布。「她是我妹妹。」
这句话就这么脱口而出。
欧拉克看看她,但是他没笑。我们互相看了一会儿,然后分道扬镳。
之后,我们看到灰脸不说话的琼恩。他坐在人行道上,背靠著一栋被炸毁大楼的残缺墙壁。「哈啰,琼恩。」我说。
琼恩好像没有听到我。他的眼睛闭著。
「他在睡觉。」亚妮娜悄悄说。
这时琼恩的一只眼睛突然睁开。「这是亚妮娜‧米格兰。」我说。
亚妮娜伸出手,说:「哈啰。」
那只眼睛又闭上了。
我在亚妮娜的耳边轻声说:「他不会说话。」
亚妮娜把我拉开,说:「让他睡觉吧。」
我提高声量,仿佛我们已经离琼恩很远,说:「她是我妹妹。」
我们走远后,我对亚妮娜说:「琼恩皮肤灰灰的,他生病了。」
亚妮娜问:「你为什么跟他们说我是你妹妹?我根本不是你妹妹。」
我耸耸肩。我也不知道。
我们回到尼斯卡街之前,听到一个巷子里传来尖叫和呼喊的声音。一群小孩缠在地上扭打。突然间,一个男孩从那团混乱中跳了出来,朝我们这边跑过来。他跑过我们身边时,我可以看到他手上抓著一颗马铃薯。有些小孩跑去追他,其他小孩则无精打采地朝巷子的另一边走了。
亚妮娜看著我,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命不好的孤儿。」我说。我跟她说伊诺斯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不住在柯查克医师那里的孤儿,或是其他在街上流浪的孤儿,又饿又病,只能乞讨。
「幸好我们不是命不好的孤儿。」我说。
「灰脸琼恩是命不好的孤儿吗?」她问。
「噢,不是。」我说,「他命很好。他跟我们在一起。」
18 冬
我们在墙内的第一个早上,乌里就找到我们了。但是现在我们更少见到他了。
「你会去墙的另外一边吗?」我问,「你有工作许可吗?」
「不要问。」他说。
一个大冷天,乌里和我在街上晃荡。我穿著两件外套,但是不管怎样也没办法让我的脚变温暖。街上有很多人。我看到一个男孩。至少从他的个子大小来看,我觉得他是个男孩。他躺在人行道上。街上那么多噪音和行人,我真纳闷他怎么睡得著。
实在很奇怪。因为他不是睡在屋子的门口,我常看到有人睡在屋子门口。他也不是睡在人行道旁,而是在人行道的正中央。行人都绕过他,在人流中空出一个眼睛的形状。奇怪的是,虽然像是没人看到他,但是也没有人被他绊倒。
而最奇怪的是报纸。一张报纸像毯子般盖著他。
「乌里,」我说,「这男孩真笨。报纸根本不够暖啊。」
「没有东西能让他温暖了,」乌里说,「他已经死了。」
我们停下来,低头看著那死掉的男孩,是唯一不这么走过去的行人。
「他为什么死了呢?」我问,「有大黑靴对他开枪吗?」
乌里耸耸肩。「也许。或者是没吃的,或者是太冷了,或者是斑疹伤寒,都有可能。」
「什么是斑疹伤寒?」
「一种病。很常见。」
「命不好的孤儿。」
「对。」
他拉著我往前走。
从此以后,我每天都看到用报纸盖住的死人。如果是小孩,很容易辨别——小孩只需要一张报纸就可以盖住了。
一天,我问乌里:「为什么他们都用报纸盖著呢?」
「这样就没有人会看到他们了。」
「但是我看得到他们。」我说。
乌里没回话。
然后我看到有个死人被人看到,被一个男人看到。他在一个死人前停下来,把脚放在报纸上绑鞋带。
同样的尸体从来没有连续两天躺在地上,但是总是有新的尸体躺在新的地方。有时他们的脚会从报纸下露出来。第一天,脚上总是有鞋,之后就不见了。然后连袜子也不见了。
晚上,我常常纳闷是谁把报纸放在尸体上,又是谁把尸体运走。
我心想:是天使。
我和男孩们,我们一起睡在碎砖瓦中。我们没有被子,但是有一个边边有穗带的圆形毯子。我们全睡在里面。不过这还不是我们最主要的被子。我们最主要的被子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手互相抱著彼此,鼻子贴在下一个人的脖子上。伊诺斯说这是交换虱子。如果哪个人放屁,他就会被赶出被子。乌里和我们在一起时,我总是睡在他旁边。但是很多的晚上他都不在。我真纳闷他都睡哪里,但是他叫我别问,所以我也没问。
我们这群男孩是挤在一团的小猫。我们是黑夜中的声音。我们常讲到母亲。虽然我不记得自己的母亲,但妈妈应该是什么样,我有很清楚的想法。但费尔迪就不是了。他总是说:
「我不相信有母亲。」
「那你觉得你是怎么来的?」一天晚上,伊诺斯在毯子下问,「大象生出来的?」
「那你以为那些握著小孩的手的女士是谁?」欧拉克问。
「冒充的。」费尔迪说。他的回答从来不会太长。他从嘴巴里吐出的烟比话还多。
「每个人都有一个母亲。」库巴说,「每一个人。」
「孤儿例外。」费尔迪说。每次他开口说话,你都可以闻到他嘴里的烟味。
「孤儿也有母亲,笨蛋。」伊诺斯说,「只是她们都死了,就这样。」
「真正的母亲不会死。」费尔迪说。
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开始讲起柳橙。就像母亲一样,柳橙也是一个我们常讲到的话题。伊诺斯说他已经吃过很多次柳橙,但是费尔迪说他在胡编。
「柳橙吃起来像什么?」我问伊诺斯。
他闭起眼睛,说:「什么都不像。」
「那柳橙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像一个下山前的小太阳。」
费尔迪说:「柳橙根本不存在。」
在早晨的阳光里,我们大多数又会开始相信母亲和柳橙,但是现在,在漆黑中的毯子下,听著从墙的另一边传来的模糊城市声响,费尔迪让我们又开始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