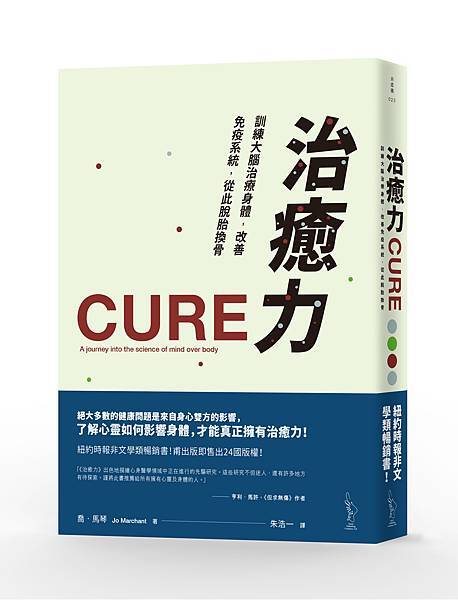《治愈力》摘文 : 对抗疲劳
你是否常常觉得疲倦,与是否有足够的休息并无关。没有来由的各种警讯…发烧、头痛、盗汗、腹痛…而辗转于多名医师、多家病院,看遍脑科、肠胃科、内分泌科、身心科后仍旧一筹莫展。
慢性疲劳症候群是医学界最具争议的疾病之一。研究学者、医师及患者对它的病名、定义甚至存在与否都有歧异。这种疾病的复元状况很差。一份二○○五年进行的试验分析追踪了罹病最长达五年的患者,结果显示此病症的复元率只有百分之五
《治愈力》透过大量案例,提出以「认知行为治疗」,由心理与生理共同对抗慢性疲劳症候群的另种可能…
「简直就被活埋了一样。」莎曼珊.米勒语气平淡地说。她的蓝眼睛盯著我,嘴里咀嚼著炸豆丸子。「我当时累坏了,关节又痛得要死,就像是得了久病不愈的感冒一样。我什么也做不了。我被困住了。」
今天,四十六岁的莎曼珊看起来青春洋溢,生气勃勃。她身上穿著一件一九五○年代风格的衣服,一尘不染的粉红色上衣还点缀著花朵图样。她头上戴了顶蓬松的贝雷帽,唇彩鲜艳明亮;一头烫得鬈鬈的金发相当漂亮,还用康乃馨定型。我们在伦敦上街里的一家具有时尚风味的土耳其餐馆里吃午餐。走路的时候,她看起来精神奕奕、风趣幽默而且反应非常快。很难想像她才刚从数年身处地狱般的日子里挣扎著回到现在的生活。
一九九○年代末,住在伦敦汉普斯特区的莎曼珊在一间「人手不足,资金短缺」的中学教艺术课。她发现应付孩子很累。孩童仍保有「无懈可击的青春年华,」她说,「他们还没有被任何事情压垮过。」莎曼珊也热中在山区里骑自行车以及游泳,社交生活亦相当活络。如果别人有什么事情没做完,她会揽过来把事情做好。她总是追求完美。
后来她生病了。「我的淋巴腺肿了起来,是病毒搞的鬼,」她说。她觉得没必要为这种事情请假。「我严重发烧。事情从那一刻开始变了样。」虽然病好了,但后来她老觉得昏沉想睡。几年过去,她到一家医院动背部手术。住院期间,她染上了肠炎。「超惨的,」她说,「到处都有东西在攻击我的身体。」
手术的伤口好了,肠炎也没事了,她却开始起不了床。她觉得筋疲力竭却睡不著觉,身体痛个不停,对声音跟光线都很敏感。由于没办法下楼,她的伴侣会在上班前在床边放些水果给她吃。她觉得自己变得很脆弱,不知所措,她没办法坐著,没办法听收音机,也没办法应门(回想过去,她说如果自己当时换成双脚无力,坐在轮椅上,至少还有力气可以去开门)。
每当她想要鞭策自己,症状就会变得更糟。因此她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记下房间里的每一道裂缝,同时凝望著墙上的一幅大画 —那幅牛津郡的风景图是她自己画的。「真不敢相信那是我画的,以后哪有办法再去做任何事情呢?」
虽然伴侣理解她的处境,但她觉得朋友跟家人都没办法谅解。他们会说些类似「我也是随时都累得半死啊」的话,而且她知道,他们认为她是自己选择卧病在床的。最教她心痛的,是她父亲说,「我觉得很烦,妳也差不多该好了吧。」失去了生活,失去了痊愈的希望,莎曼珊找来伴侣跟孪生妹妹。她希望他们帮助她自杀。
慢性疲劳症候群是医学界最具争议的疾病之一。研究学者、医师及患者对它的病名、定义甚至存在与否都有歧异。这种疾病的复元状况很差。一份二○○五年进行的试验分析追踪了罹病最长达五年的患者,结果显示此病症的复元率只有百分之五。
这种疾病是在二十世纪时,因为出现一连串导致大量民众没来由地觉得虚弱且疲累的神秘疾病,才引起医生注意。两次特别严重的爆发分别发生于一九五 ○年代伦敦皇家自由医院,以及一九八 ○年代内华达州太浩湖地区(当时的美国人为此疾病取了个别名,叫「红发安症候群 」)。后来其他地方的医生也开始接到一些突然出现的零星案例。
慢性疲劳症候群也称为肌痛性脑脊髓炎(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两种疾病有相同的症状)。此病无明确成因,也没有既定的诊断方式 ,但其症状被界定为六个月以上的长期疲劳,不仅生活受到干扰,休息也不会好转。症状包含记忆力或注意力受损、喉咙疼痛、疼痛性淋巴腺肿大、头痛,以及关节和肌肉疼痛。在如莎曼珊这样的严重案例中,患者必须长时间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这种疾病的症状跟流感很像。而且在许多案例中,慢性疲劳症候群看起来似乎是因为诸如淋巴腺热(虽然淋巴腺热跟流感不同)等病毒感染所引起的。身体似乎是清除了病毒的感染,但疲倦感却残留下来。从成人的案例来看,在罹患淋巴腺热之后,约有百分之十二的人会在六个月以后产生慢性疲劳症候群 。
由于缺乏明确的生理机制,使得这种疾病经常被认为乃由心理因素所导致:一九七○年代的精神科医师将其归结为「集体歇斯底里」,而一九八○年代的媒体则残忍地称其为「雅痞流感」,暗讽此病的患者都是些娇生惯养、懒惰而不愿工作的年轻人。医疗机构现在都同意这是一种独立的疾病,即使成因仍有争议,但许多患者依然觉得医师会把他们当作罹患焦虑病症的人对待,因此并不把他们的病当一回事,只会要他们打起精神好好过日子。
在见过一些罹患慢性疲劳症候群的运动员以后,诺克斯对这种疾病产生了兴趣,并发现他们的状况并不符合传统说法。「我见过太多还想跑步的职业运动员,他们正在失去一切,然而他们仍旧跑不动,」他说。「而他们最不想要的就是生病。」
他相信这种疾病的成因就藏在大脑中。「控制中枢的设定出了问题,错估了疲累程度。」多数跟控制中枢理论有关的研究都牵涉到体能极限的微妙改变,通常都发生在顶尖运动员身上。但如果整套系统坏了会发生什么事呢?通常用来保护我们免于运动过度的疲劳或许反而会成为一副枷锁。
无论成因为何—病毒、过劳、遗传体质,或(最有可能的)多种因素的总和—诺克斯说,罹患慢性疲劳症候群后,身体能够活动的限度会大幅缩减,致使病人几乎无法行动。如果他的理论正确的话,就代表像莎曼珊这样的患者无法「决定」自己想要变得更有活力,就如同梅斯涅无法在圣母峰的峰顶跳一支吉格舞 ,或法拉无法将伦敦奥运会夺得金牌的时间再减少二十秒一样。
但这也暗示了他们的症状可能会受到心理因素影响。的确,在跟慢性疲劳症候群有关的科学发现中,最强而有力的其中一个就是,当患者相信自己的症状源于生理因素、无法治疗,而且担心参与任何活动都有可能使病况恶化时,康复的机率会降低许多。「如果他们相信治不好,就真的治不好。」诺克斯说。虽然身体发出的讯息显然对我们决定自己是否疲累至关重要,但最后做决定的依然是大脑。
这就引发了另一个问题:是否有办法透过认知治疗跟行为治疗慢慢将大脑过于苛刻的限制往后拉。如果间歇训练能够帮助运动员,教导其控制中枢,其实难度更高的运动仍然安全无虞,那么或许这样的方法也能够套用在慢性疲劳症候群的患者身上?
莎曼珊跟伴侣及妹妹做了一个约定。她被转诊到伦敦圣巴索罗缪医院专科医师彼得.怀特的手中。只要给他六个月的时间就好,他们说。如果妳觉得病情还是没有起色,我们会帮妳结束性命。
与诺克斯无关,针对慢性疲劳症候群,怀特也发展出了类似的想法。他不称它为控制中枢,但他认为是一些原因—基因、环境、心理—综合起来压垮了身体,使得神经系统失衡,让脑部大幅缩减它认定的身体活动安全限度。为了要逆转这样的改变,他跟同事一起发展出一套渐进式运动疗法。这种疗法的功用跟间歇训练很像,只不过难度变得非常非常低。
其概念是设立一个让患者可以安全运动的底线,再逐步增加强度。每一次都不能前进得太快,但同时也得注意不能让患者回到先前的状态。根据慢性疲劳症候群患者的说法,比起健康的人而言,只需要一定程度的运动,就能让他们觉得万分疲累。但怀特指出,在完成渐进式运动疗法的疗程以后,虽然体能没有改变,但若再做一次等量的运动,他们的疲劳程度却会减轻。就如同运动员会重复冲刺一样,这种运动方式能够缓慢地重新训练患者的大脑,让大脑知道每一次疗程里所做的一连串运动强度都在安全范围内。
同时,怀特也会采用认知行为治疗。所谓的认知行为治疗,就是治疗师会跟患者一起对抗他们对自身疾病所抱持的负面认知及想法。会这么做的根据在于,研究发现,如果患者害怕任何费劲的运动都会使得身体随之崩塌的话,疲倦就会如老虎钳般继续紧咬不放。认知行为治疗能够鼓励他们试著换换不同的想法,用不同的心态面对自己的疾病,并要他们测试自己的身体是否能够承受些许的运动。治疗师希望透过这种方式减轻他们的恐惧,帮助他们认清或许稍微费点力气的运动终究是安全的,他们仍有机会痊愈。
怀特建议莎曼珊试试综合渐进式运动疗法与认知行为治疗。「我的状况会改善吗?」莎曼珊问治疗师。「当然啦。」她说。莎曼珊第一次相信这真的有可能会发生。
她的第一个运动目标很简单:每小时在床上翻身一次。每隔几天,治疗师都会稍微增加运动的强度,直到能够一次坐五分钟为止。接著,在她能够下床以后,她会试试烹调餐点,这件事会分成好几个部分:下楼、切洋葱、上楼、躺下。身为一个有创意脑袋的人,她发现自己很难接受这些完全缺乏自发性的行为,但那导致她生病的完美主义就在此时帮上忙。
她有一本运动日记,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以后,她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我能在街上散步两分钟,」她回忆。「接著是三分钟。但如果走五分钟的话,我可能就得在床上躺三个星期。」她得按照计划走,不管觉得自己情况有多好,都要遵照医师规定的强度去做,不要做太多,但也不能做太少。
如果她让自己太劳累,身体会承受不了。「我得要非常自制,」她说。「走错一步,我就回到起点。」如果她破坏规定,试图做更多运动,就会开始觉得身体不听使唤。「会从脚底开始感受到一阵热度,简直就像有人对我下毒一样,然后我就得瘫在床上好几个星期。」
在强韧的意志力坚持下,她花了五年的时间,总算爬出了疲倦的牢笼,回到正常的人生。
几个小型的临床试验暗示莎曼珊或许并不孤单。试验结果显示认知行为治疗及渐进式运动疗法的确有帮助。然而,病友团体非但不喜欢这些发现,甚至还痛恨它们。「几乎所有英国及海外那些帮助慢性疲劳症候群募款的慈善团体都不喜欢这个结论。」怀特说。这些团体非常怀疑类似认知行为治疗的这种「心理」疗法有办法帮助罹患慢性疲劳症候群的人,并且相信渐进式运动疗法的运动目标极其危险。他们说,慢性疲劳症候群单纯就是一种找不到明确治疗方式的生理疾病,因此任何接受怀特的治疗以后病情有所进展的人显然没有罹患这种病。
取而代之的是,病友团体推崇一种称为慢行的生活方式。虽然患者的体能因慢性疲劳症候群而受到限制,但慢行能够帮助患者适应这种受限的生活,同时鼓励他们不要做任何会让自己太累的事情。如果慢性疲劳症候群是一种不治之症,这样的做法的确非常合理。但根据怀特的理论,这种做法会带来相反的效果。慢行会强化患者的负面思维,让患者的病症维持在原点,而非帮助他们痊愈。
谁是对的?怀特跟他的同事决定要做一场决定性的试验。他们跟英国最大的疾病慈善团体「抢救肌痛性脑脊髓炎」合作,设计并进行一场长达五年的研究。这项研究计划包含六百四十一名患者,共分成四组。单一对照组只接受一般的医疗—建议避免激烈运动,加上针对各症状诸如忧郁、失眠及疼痛等开立药物。其他组则除了一般医疗之外,各别再加上认知行为治疗、渐进式运动疗法,或是由慢行发展而来的适应性步调疗法。
研究学者于二○一一年将结果发表在医学期刊《刺胳针》上。他们发现适应性步调疗法毫无任何疗效;这组患者○的表现并没有优于对照组。但是渐进式运动疗法与认知行为治疗都有一定的功效。相较于另外两组,这两组患者的疲劳及行动不便指数都有显著下降。不只如此,在接受认知行为治疗与渐进式运动疗法后,有百分之二十二的患者痊愈了,另外两组的痊愈率仅百分之七到八。虽然不算大成功,结果却显示出怀特的治疗方式是目前最有效的,而且证实了这种疾病有办法治愈。
若说先前的试验结果不受欢迎,这次的结果则是引来极端的愤怒。《刺胳针》收到潮水般的批评信件,全部都是在批评怀特的治疗方法。抢救肌痛性脑脊髓炎团体拒绝相信这次的发现。其中一名教授写了封长达四十三页的抱怨信寄到《刺胳针》,信中指出这场试验「既不道德又不科学」。同时,患者则利用脸书发问:《刺胳针》《刺胳针》什么时候才要撤回这场骗人的研究?」
情况正好相反。《刺胳针》发表了一封编辑信,信中支持怀特及其同事,并说他们「应该要因为愿意测试其他竞争想法,以及在随机对照试验中所受到的干预而获得赞扬」。但这封信并没有改变病友团体的态度,在经历多年找赞助、规划及进行决定性试验后,怀特终于收集到他相信足以帮助像莎曼珊这种慢性疲劳症候群患者的资料。来找他看病的患者都欣然接受他的发现,但他却说服不了由肌痛性脑脊髓炎患者所组成的团体。
至今,关于慢性疲劳症候群是生理或是心理疾病的争论仍沸沸扬扬。二○一四年六月,两名来自英国绍森德大学医院艾塞克斯郡慢性疲劳症候群/肌痛性脑脊髓炎服务中心的学者在《英国医学期刊》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推测慢性疲劳症候群可能是一种「弥」。这个词是由遗传学家理察.道金斯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所发明,用来形容一种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播的心理或行为。
该文的两位作者认为,历史上有几种医学疾病都有可能是由弥所引起的,例如「铁道型脑损伤」,这是一种综合疲劳及精神症状的疾病,对十九世纪搭火车旅行的人带来了影响(火车是当时的新发明),同时代的人认为可能是由于乘车过程过于颠簸而无形中造成了脑部的损伤。他们说,慢性疲劳症候群的某些症状可能也透过类似弥的方式扩散出去。
在当时,立即出现要求撤除该篇文章的活动。肌痛性脑脊髓炎协会提到他们的成员对这种说法感到讶异、愤怒及担心。在该篇线上文章的回应区里,慢性疲劳症候群的患者控诉文章作者「自大、偏执、十分残忍」。同时,他们的论点被斥为「骇人听闻」、「扭曲又病态」以及「疯狂透顶」。几天过后,艾塞克斯慢性疲劳症候群/肌痛性脑脊髓炎服务中心写了一封信到肌痛性脑脊髓炎协会,表明这篇文章的立场与服务中心无关,并说两名作者「对于自己可能造成的不便感到万分抱歉」。
根据怀特的说法,问题一直都出在医学界随处可见的惯有思维:疾病若非来自生理问题,就是来自心理问题。「大多数的医师都将心灵及身体拆成两边来看,」他说。「心理问题,就去看精神科。生理问题,就看一般医师。」这种分类方式让慢性疲劳症候群只有两个选择—若不是罹患了跟心理因素毫无关系、只是目前还没办法治愈的生理性疾病,就是得了虑病症,所有的症状都是自己幻想出来的,难怪防备心会这么重。
怀特说,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的分类方式。心灵与身体的互动是必然的,而且两者会相互影响:「跟心理有关的,一定也跟生理有关,任何生理问题都有其心理的层面。」科学家逐渐发现,诸如思觉失调症或忧郁症等精神疾病,都会反映到脑部的结构异常,而神经性疾病如帕金森氏症会同时产生心理与生理的症状。
怀特指出,虽然人们认为行为治疗是属于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但它也能对身体带来生理影响。例如,一些研究发现,在做完认知行为治疗的疗程以后,大脑的质量会有显著的增加,或能够影响如皮质醇一类的压力荷尔蒙浓度。
他认为,如果罹患慢性疲劳症候群的人能够在态度上有较大的转变,或许能让他们接受自身的疾病乃结合生理与心理双方面的成因,而无须担心遭到污名化。慢性疲劳症候群既非生理疾病,也非精神疾病。它是两者的结合。
莎曼珊的慢性疲劳症候群已经治好两年了。「我做的事情比同年龄的女性多很多,」说这话的同时,她撕了薄饼去沾鹰嘴豆泥。「我是骑脚踏车过来的,我成功地让自己的装扮看起来不会太突兀!」她还是得当心,如果骑得太费劲,或是工作压力太大,都有可能使她再次发病。「我不管身体还是心理,我都得保留一分余地。」她说。
因此,现在如果她生病,就会请病假,而且也懂得说「不」。她兼差当艺术治疗师,带著狱囚及罹患诸如躁郁症和思觉失调症等精神疾病的人做陶艺。她说,做陶艺能够提供他们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他们得以说说话。「如果聊得不顺,还可以立刻回去继续捏陶土。」
她同时也是一名艺术家 。在一系列的作品中,她将老旧的纪念品 —娃娃、松果、动物头骨 —整整齐齐地放置在装饰过的框架里。她说,她喜欢拯救那些曾经被人当作宝贝、如今成了累赘的东西,然后赋予它们新生命跟意义。她也画画,画些萦绕心中久久不去的景象,包括一幅用灰黑色及血红色病床和拱窗排列而成的迷宫,交叠写上汤玛斯.哈代诗作《朦胧的画眉》的头几行:「身倚栅篱往外望,灰白冰霜鬼魅样。冬雪大地满凄凉,昼日昏暗犹无光。」
这首诗的结尾是虚弱衰老的画眉唱著欢快的曲调,在带来死亡的黑色寒冬中,正是「幸福希望」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