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林观点:回归快乐—乐生疗养院

乐生旧大门残骸(门柱已于今年四月遭捷运局无预警拆除)(作者提供)
在2017年12月29日一个阴冷的落雨下午,我拜访了位于新北市西南一角与桃园相邻的乐生旧院区。带著悲伤,我站在标有地址的旧大门残骸近旁,该处巨大的悬空陆桥与捷运机厂正在进行建设。我看见山丘被割裂,那就像大地母亲身上的一道伤口,而仍有人居的旧院区在遥远的丘顶,被这人为的裂痕与邻近马路的大门永久分离。看见台湾的重要文化遗产竟受此待遇,我的内心没有幸福,思绪也无法平静。这项文化遗产承载著具普世价值的人类记忆,而那记忆关于苦难也关于希望。
重要遗产
乐生对台湾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与环境价值,它由日本殖民地政府于1929年昭和时期建立,名为“Taiwan Sofokufu Raibyou Rakuseiin(台湾总督府癞病疗养乐生院)”,自1934年以来一直被日本人用做强制性隔离设施,随后由国民党政府接续。到了1940年代有效治疗痲疯病的药物终于被发明,而该疾病也被视为得以治愈。1954年后,居住于乐生疗养院的院民可以自由离开,但许多人更乐意在这具紧密联系的社群里待到今天。
乐生在文化上也有其重要性,它见证了人类所蒙受的苦难与污名、疾病与治愈的历史、隔离与庇护机构、日本昭和时期在台湾的建筑风格与疗养院型态,与其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痲疯病相关遗址具有同等重要价值,这些遗址包含有勃艮第的默索尔勒索麻疯病院(Leproserie de Meursault),澳大利亚大堡礁的芬托姆岛(Fantome Island),南非的罗本岛(Robben Island),威尼斯的圣拉扎罗德利阿梅尼岛(Island of San Lazzaro degli Armeni),澳门的圣拉撒路区(Sint Lazarus district)等等。
在环境上,乐生座落于树丛茂密的山丘,为台北市形成了天然的缓冲区,也为水资源保留以及生态多样性提供了重要条件,是我们抵抗气候变迁以及过度开发的最后防御。同时,它却位处台湾断层带上,这增添了乐生在面对地震和山崩时的脆弱性。
1994年一场不幸的发展直接冲击了乐生,捷运新庄机厂的建设计划决定挖空易碎山丘,并切割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方完整性。自此之后,保留与发展的冲突便持续酝酿,而利害相关者之间透过民主程序所达成的共识仍旧遥遥无期。缺乏共识、缺乏有效的保留与管理机制(如历史城市景观和遗产影响评估),已经将乐生(无论国内或国际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遗产)置于不可逆的毁灭危机。
包含医院主楼在内的大量建筑被摧毁或拆除,一些幸存的建物,则因不受监管的走山,以及捷运新庄机厂施工时所发生的震动产生裂痕,处于毁坏边缘。由山脚下通往乐生旧院区的道路狭窄、蜿蜒,对于居民以及拜访者来说都相当不方便。正在建造的巨大钢桥看起来并不能够解决文化景观完整性问题、环境问题,以及乐生院民在社会心理学上的创伤。

同理心与道德
值得赞扬的是,为了保护重要遗产免受持续恶化与破坏,地方志愿者以及学者专家努力倡议许多替代方案。这彰显出在台湾,各色人士与群体对乐生这一社群的强烈同情与团结,他们力挺乐生院民继续居住在旧院区的意愿。
在那个拜访乐生的落雨下午,我遇上了一些院民并与他们交谈,言谈中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希望能够继续在此居住的渴望。院民并不自私,他们相当慷慨地分享生命故事,并热情款待所有到访者。
最让我感动的时刻,我和同是院民之一的茆万枝先生的会面。茆先生坚持要带所有到访者参观他的「博物馆」,这间博物馆就位于一栋旧院舍中。这是一次叫人吃惊的体验,当我看到每一栋建筑物的模型设计图,以及细节丰富的乐生大型模型,我可以感受到茆先生的爱、关怀与哀伤,但同时也感受到他的希望和抵抗破坏与遗忘的正面能量。

他向我展示他的一只木箱,当中收藏有被拆除的医院建筑模型,这个模型总是被茆先生带著一起参加各种大小场合,不论是和平抗争、会见政府与公司官员,又或者与拜访乐生者闲谈。在这房间的角落,他甚至保留有过世友人的遗物:旧手提箱,以及各项当年被迫搬进疗养院时随身携带杂物、衣服、裁缝机还有其余物品,见到此情此景让我感到伤心。

这位谦逊的老人家过去受汉生病所苦,他代表著乐生坚韧不摧的精神,他提醒著我们爱护与尊重过去遗产的重要性,如同照料我们的年迈父母,如此他们才能持续向我们以及未来世代传达道德、人道、社会正义这些基本的普世价值。茆先生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具有正确态度的人,不受经济利益束缚亦不受贪婪暴政蒙蔽。突然之间,对我来说一切都变得相当明朗,迫迁乐生社群、捣毁他们的居所,就如同残酷地对待我们的父母以及祖传土地,违背了所有宗教以及我们的传统所教授的基本道德。
实际行动
目前最急迫而须立即采取的行动是,监督并阻止走山恶化,保护山丘、道路以及避免幸存的乐生建筑受到进一步的损毁。同等重要的是重申前疗养院作为国家文化景观的法律地位,以使其受到保护,并保护旧院区内的其余原始建筑,也就是连接道路并载有门牌号码的旧大门必须不受毁坏与拆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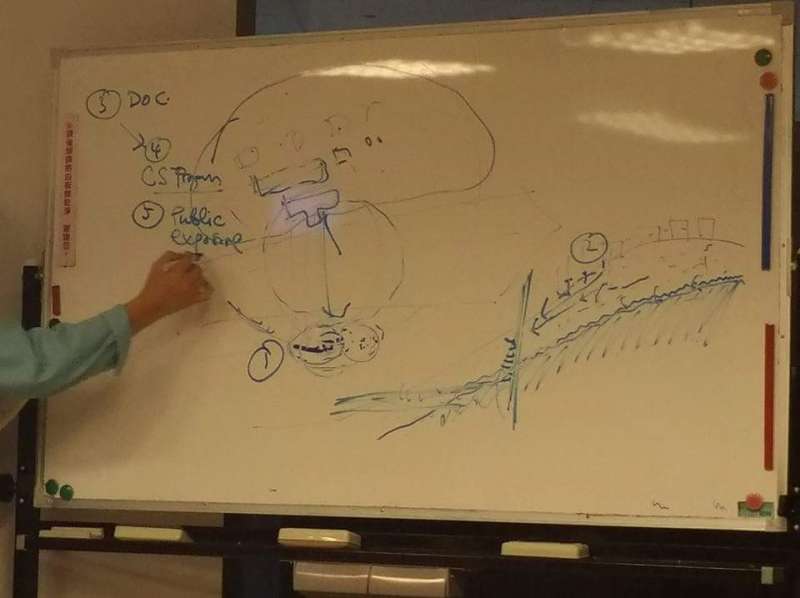
下一步,必须对现存建物做出全面建档、清查并绘制所有现存建物的测量图,茆先生的设计图与模型是相当重要的起点,原件必须被妥善保存,并建立电子档。过去被拆除的建物相关文件必须被收集,而现有的原始材料(例如:瓦片、地砖与墙砖、木料、砖头、钢铁等等)得要受到保留,以便在日后重建工作中有被重新使用的可能。
有了这些完整文件做基础,台湾的大学以及国际伙伴间将能够启动多边工作计划,聚焦在为乐生保存以及恰当地再利用制订发展方针与设计提案,并且拉近、缝补因为捷运新庄机厂的建设而造成的人为断层。须注意的是,多边合作需透过文件、多边工作室、设计竞赛、公开展览和控管,连结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志工以及各相关单位(例如:台北大众捷运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部)。
计划与设计提案将对现存空间与建筑采适切重起的途径,以在不断变化的脉络和经济可行性(economic viability)下保留文化与建物的原真。对现址的规划、设计须能够揭示此地的底蕴,包含乐生的历史、建筑、文化、社会以及环境的重要性。新的功能必须在现存旧址、建筑、群集中增加经济可行性,并以兼容、适切的方式回应当下的物质、社会与环境脉络。新的设计与人为介入必须与现有建筑、自然条件在象征性、物质层面、美感以及功能上良好地并存。
多边工作计划(或开放设计竞赛)的结果应该公开透明,让公众得以检视并获得说明,且须促进利害关系人间的对话。如此一来,我们方得以获得选出最可被接受想法或概念的基础,而这将被更进一步转化为官方计划、设计与执行过程的摘要。各方应坚守透明性、可问责性以及民主。
以上工作都必须被有系统地记录下来,加上完整的文件整理、对乐生卓越普世价值的坚定表述,很可能将为此地名列国家或世界遗产登记立下基础(例如:借由跨国合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提交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等)。
回归快乐
乐生二字的意涵是「快乐的人生」。在短暂的拜访后,我无法停止思考让乐生社群回归快乐人生的方法。我了解自1994年来的情况:院民们老迈凋零,仍旧居住在老房子里的人数逐渐减少、在2001-2002年间建设新医院并迫迁乐生院民、2004年倡议以大平台方案重新连结院民居所与主要道路,并要求捷运减轨、决定保留29栋建筑物以及重建2007年前拆除的10栋建筑、支持保留方与支持开发方持续至今的冲突。
保存有形和无形的遗产无可否认是重要的,但我们同样也无法否认经济成长与调节、适应不断变化生活型态的必要性。扩大大规模公共交通系统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重要且必须,但这件事可以受到更好的管理。对遗产的保存与发展并不是相互违背的,只要整个过程能够被理解为管理方式的变革,在这项变革中所有利害相关者都必须公开透明且具可问责性地参与。

在这短暂拜访台北的期间,我与立法院蔡培慧女士、文化部主任秘书(译者注:时任)陈济民先生和文资司司长(译者注:现任主任秘书)陈登钦先生、台北市律师公会的年轻成员,以及台北市中山公民会馆的民众都有所交流,这给了我一种乐观的感受,并希望下一阶段的发展能够朝向积极的方向。在台湾许多人与政党都同意,保存乐生的完整具有重要性,这不只为了台湾,也为了世界。
在保存重要但脆弱遗产的斗争过程中,乐生与台湾人并不孤单,国家或者跨国组织都会与你们并肩作战,这些组织包括ICOMOS(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Docomomo(现代运动建筑,遗址和社区文献和保护国际委员会)、OWHC-AP(世界遗产城市组织-亚太地区)、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mAAN(现代亚洲建筑网),各个国家的遗产基金会和社团等也可以为台湾提供协助。
只有来自当今世代利害相关者的爱、尊重与慷慨,才能延长乐生的年岁,并将其以良好的态样移交给下一个世代,教导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同理心与善良。
*作者Dr. Johannes Widodo为马来西亚马六甲TTCL亚洲建筑和城市遗产中心副教授与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建筑杂志执行编辑、mAAN(现代亚洲建筑网)创办人、iNTA(国际热带建筑网)创办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评审委员会委员、新加坡ICOMOS国家委员会主任、亚洲遗产管理学院副主任、澳门DoCoMoMo主任、新加坡国家文物保护局遗址和古迹保护顾问委员会成员、mASEANa(现代东南亚国家协会建筑学)项目执行长。本文译者为郑皓中,毕业于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