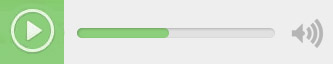李歐梵丨如何聽馬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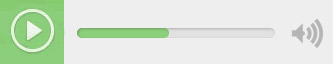
如何聽馬勒
2011年是「馬勒年」──作曲家馬勒(1860-1911)逝世的100週年,世界各地都有大量的紀念活動,各交響樂團演奏他的九首半(《第十交響曲》沒有完成)交響曲和《大地之歌》,新發行的唱碟當然不計其數,我個人就先後購了不下數十張。
聽馬勒的音樂很自然會想要了解他的一生,不少樂迷問我,應該看什麼書。我一時想不出有什麼中文本可看,現在有了答案,就是這本剛出籠的《憶馬勒》,著者是他的夫人阿爾瑪?馬勒(1879-1964),書中還收羅了馬勒致阿爾瑪的大量書信,彌足珍貴。
然而,作為馬勒迷,我對此書的敘述和論點不無偏見。我的態度,就像目睹一對好友夫妻離婚一樣,表面上置身事外,保持中立,但內心不無偏袒。對我而言,阿爾瑪文中也充滿了愛意和人情味,把一個活生生的作曲家的各面――他的藝術、性格、行為舉止,甚至夫妻關係中的性無能問題(後被弗洛伊德一席長談治癒)――暴露無遺。令我讀時最為感動的一段是長女的死亡,夫婦二人痛不欲生,誰看了不會動容?
這類第一手資料,非當事人不能完全領會。然而阿爾瑪並非等閑人物,她自己也是作曲家,而且創作過近百首藝術歌曲,但她的作曲才華卻被埋沒於這段婚姻,因為馬勒在娶她時就約法三章:不準作曲,只能為他抄譜,「從現在起你只有一個職業:使我幸福!」好一個大男人的口氣!試想這位維也納第一美女和才女如何受得了?
所以在馬勒得了不治之症即將去世的那一年,她終於和一位較她年歲更輕的建築師格羅庇烏斯發生了婚外情。她一面照顧病中的馬勒,一面和情夫魚雁往返,到處偷情,最後情夫苦苦追求到他們住處,馬勒竟然也請這位情敵登堂入室,讓阿爾瑪決定自己到底鐘意哪一個。最後阿爾瑪還是離不開丈夫。
這象是一場「肥皂剧」的情節,誰知道是真是假。即使全書真實,但馬勒在那一刻的感受如何、想的是什麼,我們都無由得知,因為以上都是出自阿爾瑪之筆。馬勒死無對證,只有《第十交響曲》原譜中的幾句向阿爾瑪示愛的話──地老天荒,此情不渝,但一般聽眾聽得出來嗎?
這就引出我的主觀偏見:藝術雖出自人生或是人生的寫照,但它畢竟不是人生,二者之間不能畫等號。阿爾瑪在這本回憶錄中也處處對馬勒的作品發表議論和詮釋,我卻不敢照單全收。例如她說馬勒的《第六交響曲》是在描寫他們一家人暑期的生活,內中還有兩個女兒的嬉戲,最後樂章中的三聲木錘巨響就像是一棵大樹被斬斷了,影射的是馬勒自己的死亡,似乎未卜先知,在曲譜中早已預言了。後世的樂評家大都蕭規曹隨,依樣葫蘆,但我就是不相信。即便是作曲家自己也作此解釋,聽者照樣不必受這種「寫實主義」詮釋法的限制。我們何不這麼說:這三聲巨響──後來改為兩聲──代表的是一種命運之力,加強了全曲的悲劇性?而這種悲劇與個人無關,是超越人生的藝術表現。曲中所謂兒童嬉戲只不過是馬勒所獨創的一種「詼諧曲」的作曲法。
Ewa Podles 演唱《亡兒之歌》
馬勒熱愛他的兩個女兒,但在家庭生活最快樂的時候卻寫下了五首《亡兒之歌》,曲中的「兒童」,阿爾瑪認為指的就是自己的女兒,這又是「對號入座」,因此她說:「當人們在半小時之前鍾愛過和親吻過那些活蹦亂跳和身體健康的孩子時,現在怎麼就能去歌唱孩子之死。」
也有人認為:馬勒悼念的是他幼年夭折的亡弟。兩者都是「索隱」式的論點,我不盡同意。我想馬勒當時的心情可能是出自一種對人生弔詭的感慨:好景不長,在最快樂的時辰也會感到憂慮。難道不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詮釋他的《大地之歌》和他的交響曲?
走筆至此,不覺已進入馬勒作品研究的境界,目前這也成了音樂界的「顯學」,我不願再班門弄斧了,就此打住。且不論以上的描述是否有理,我仍然認為對於馬勒的生平有興趣的讀者,阿爾瑪的這本《憶馬勒》是不可或缺的入門書。如果對阿爾瑪的生平興趣更大,則可讀她自己的回憶錄《我的生活》(Mein Leben,有英譯本,改名為And The Bridge Is Love──《而橋樑就是愛》)。
廖昌永演唱《亡兒之歌》
馬勒的唱碟車載斗量,又該如何向初入門者推介?最好還是聆聽現場的演奏,遠較錄音動人。不少友人問我,該從何首交響樂聽起。我的回答是:第一和第四,然後再聽第二、第三、第九和《大地之歌》,中間的第五、第六、第七則需要耐性和時間慢慢聽。我唯一不大喜歡的是他的《第八交響曲》,可以最後聽。另一個入門之道是先聽他的歌曲集:《亡兒之歌》《旅人之歌》和四首《呂克特之歌》,再聽《大地之歌》。
你的讚賞是我堅持原創的動力
讚賞共 0 人讚賞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