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社會成都的地域歧視鏈
在傳統中國城市裏,社會排斥和歧視的現象一直都存在,一個族羣或行業集團會對另一個族羣或行業集團體持敵視的態度,城市居民欺侮鄉下人的情況也很普遍。這裏“族羣”並非是指不同種族的人羣,而是指由於地理、經濟、文化、社會地位等因素造成的社會隔閡和人的羣體。
排斥和歧視激起了被排斥者、受欺侮者和受歧視者的憤怒,促使他們爲自己的權利而進行鬥爭。歧視蘇北人在上海非常典型,類似的情況在成都也存在。與上海一樣,方言、歷史和籍貫都能在人們之間劃出界限。與上海不同的是,在成都沒有特定的地域偏見,但是居民們對滿族人懷有敵意,對鄉下人持明顯的歧視態度。
成都漢人和旗人被滿城(又叫少城或內城)的城牆分隔在不同的區域,但是他們之間的衝突仍然十分頻繁。晚清時期,成都大約有四千多戶滿人,總人口一萬九千多,大都住在滿城。
 左邊的城牆內便是滿城,又叫少城
左邊的城牆內便是滿城,又叫少城地方文人在竹枝詞中有不少描繪成都滿人打獵、看戲、釣魚的生活方式:
旗人遊獵盡盤桓,
會館戲多看不難。
逢着忌辰真個空,
出城添得釣魚竿。
在城西的兵營附近,市鎮居民能看見滿族人的馬在放牧。有竹枝詞寫到成都滿人的其他嗜好:
西較場兵旗下家,
一心崇儉黜浮華。
馬腸零截小豬肉,
難等關錢賤賣花。
這是說旗人喜花,一收到月錢即買花光,但等買食物無錢時,只好賤賣花以維生。
在當地文人的作品裏,對旗人總有不少負面的描述。由於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認同,加之政治因素而產生的相互憎惡,一代代傳承下來。在晚清,地方文人指出滿人之所以變得越來越窮,是因爲他們的懶惰和閒散,一首竹枝詞寫道:
吾儕各自尋生活,
回教屠牛養一家。
只有旗人無個事,
垂綸常到夕陽斜。
另一首竹枝詞也表現了類似的抱怨:
蠶桑紡織未曾挨,
日日牌場亦快哉。
聽說北門時演戲,
牽連齊出內城來。
這是說滿人不幹活爲生,整日棋牌賭博。一聽說有戲看,便蜂擁而至。
有身份人家的少婦拒絕到少城去,因爲她們認爲那裏的人們“懶散”、“骯髒”而“粗魯”,而且老是盯着她們看。在漢人居住的“大城”裏,不斷有年輕女士在滿城受到騷擾的傳聞。當地文人在描述滿人時經常使用的語言,很清楚地反映了成都滿漢族羣之間的對抗。
族羣衝突問題在政治危機期間變得更爲突出。在1911年革命前,居住在“大城”的漢人與居住在“少城”的滿人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張,李劼人在他的小說《大波》裏便描述了這樣的矛盾。積澱了二百多年的漢滿之間的敵對終於在1911年爆發了,但是暴發導火線不是民族問題,而是與清政府的政治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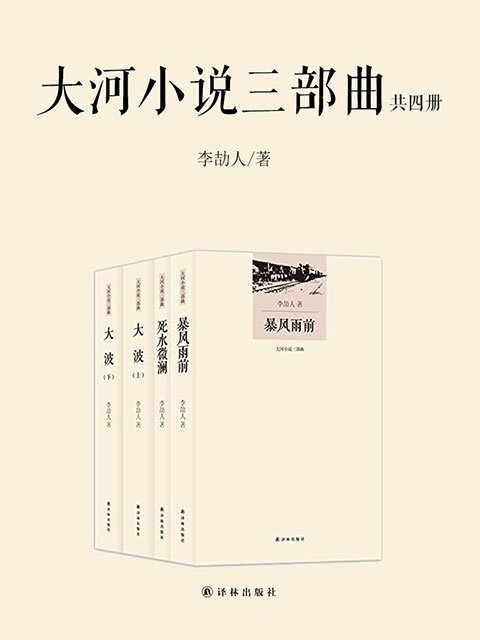
當成都宣佈獨立時,城裏的滿人聽說在西安、錦州等城市,許多滿族人被漢人殺死,他們開始爲自己的生命擔憂。決定當無法保護自己時,讓所有的婦女和孩子都自殺後,男人則去拼命。然而,新成立的軍政府承諾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沒有發生他們所恐懼的族羣間屠殺事件。
成都居民也看不起來自邊遠地區的人們,特別是那些住在四川西部邊境沿線的藏人。成都既是中草藥、毛皮和藏貨貿易的中心,也是本地商人到全國各地貿易的中轉站。成都居民將那些來自邊遠地區的人看作是“鄉巴佬”或“野蠻人”。
正如一個地方文人用諧噱的口吻所寫的:“西蜀省招蠻二姐,花纏細辮態多憨”。一位文人在其竹枝詞中,嘲笑那些來自大小金川和西藏的藏人:
大小金川前後藏,
每年冬進省城來。
酥油賣了銅錢在,
獨買鐃鉦響器回。
有意思的是這位作者爲這首竹枝詞加了個注,讓我們進一步瞭解成都市民對這些遠道而來的藏民的態度:“蜀中三面環夷,每年冬,近省蠻人多來賣酥油,回時必買銅鑼銅鐃等響器,鋪中試擊,側聽洪音,華人每笑其狀。”
對藏民來說,成都是做生意和與外部世界聯繫最近的一個重要商業中心,而成都居民也同樣依賴這些商業活動,但是經濟交往雖然能夠增進相互理解,但文化隔離和歧視卻根深蒂固,這從作者所用的“夷”、“蠻人”等詞中表露無餘。在他們的文字中,“我們”與“他們”的區分是十分清楚的。
法國年鑑學派代表人物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研究了城市與鄉村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並努力去“重新發現一種爲全世界城市都存在的共同現象”,這即是城鄉間的既相互依賴又有着隔閡的關係。他發現,“同農村持續不斷的對立似乎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
成都與臨近的鄉村有着密切的聯繫,儘管一堵城牆將城市圍了起來,但是城市居民不可避免地依賴與城外地區的交易。這樣一來,一個既相互對立又相互依靠的模式建立起來。例如,如果沒有周圍農村,城市居民便不能享用新鮮食品和僱用來自鄉下的廉價勞動力。
另外,成都平原的農戶的居住模式是分散型,每個家庭都住在他們的耕地附近,基本上不存在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村莊”。在成都平原上,田野中間被竹林環繞的一家一戶或若干農舍成爲其獨特的自然景觀。由於沒有或缺少緊密的鄰裏關係,平原上的農家們會產生一種孤獨感,因此頻繁地趕場和進城就成爲他們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之事。
 成都平原景色
成都平原景色每天都有很多人來到成都的街上、酒館和茶館裏尋求與他人的——既有經濟的亦有社會的——聯繫。而且他們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城鎮市場來交換農產品和手工業品。
在繁忙的春秋季節裏,農民們在田地間辛勤耕作;但是在夏冬農閒時,他們又作爲遊方小販或匠人出現在成都街頭。因此,在成都街頭可以定期看到來自農村的小販和手藝人,他們大多是早來晚歸,但是如果有些路程較遠的外來客,需要在城中逗留幾天或更長的時間,也會在小客棧特別是在廉價的“雞毛店”過夜。
城市居民認爲他們比鄉下人高一等,嘲笑他們“愚蠢”、“幼稚”、“粗俗”,稱他們爲“鄉巴佬”、“鄉愚”,說他們的閒話,傳播一些關於鄉下人的“離奇”故事,把他們作爲茶餘飯後譏諷的對象。儘管兩者都生活在成都平原,但他們看起來卻有極大的不同。
住在城牆外的農民——哪怕即使是離城一兩裏遠——外表、口音、穿着等與城裏人都有明顯區別。鄉下人的出現不時會引起飯館、茶館裏的城裏人許多好奇的打量甚至議論。下面是1917年發生在一個茶館裏的談話,便充分說明瞭都市人和“鄉巴佬”間的鴻溝:
昨有一個農民來省,到某茶園喫茶。聞有人說:“西南政策把我們害了”。農民上前怒謂之曰:“稀爛政策害了你們?聞省中善人很多,生的死的都被憐恤。我們鄉下人受稀爛政策的影響,銀錢衣物要搶去;莫得現銀物,人也要拉去。捱打受氣,又出錢,有哪個憐憫你?”其人見農民誤解,復謂之:“現在講的是雲南政策了”。農民更驚,旋又答之曰:“說起營盤,我輩更怕!”農民方開口,其人知不可諭,遂起而去。
漢語中有許多同音和近音詞,人們對話中因此可能出現曲解。不同口音的人交談時,這種情況就更爲嚴重。從表面上看,這個故事是關於那農民對城裏人談話一些近音詞的誤解,但弦外之音,卻是與“愚蠢”的農民無法進行“政治話題”的談論,進一步反映出城市居民的優越感。從“其人知不可諭,遂起而去”來看,這個城裏人是不屑與這個“鄉巴佬”費口水,乾脆一走了之。
不過,這個在茶館的插曲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瞭,在軍閥時期人們仍然可以在茶館中進行無拘束的閒聊,哪怕是農民,也可以隨便插入他人的談話。然而,在國民黨時代,這種自由受到極大的限制,恐怕惹麻煩的店主總是貼出“休談國事”的告白,以警告人們在各茶館中不要議論敏感話題。
除了城鄉衝突之外,新老移民之間的對立在中國城市裏也很普遍。由於明末清初戰爭之破壞,成都幾乎很少有真正的本地人。清初以來,通過不斷地移民,城市恢復了昔日的繁榮。地方文人吳好山寫道:
三年五載總依依,
來者頗多去者稀。
不是成都風景好,
異鄉焉得競忘歸。
來自外省的大批商人到了成都後就逐漸定居下來,開店營業,他們大多數人都專營一種或者幾種商品。隨着他們人數的增加,他們建立了行會或會館。
 會館
會館對於移民來說,成都有更多謀生的機會,特別是對那些因自然災害和土匪橫行而背井離鄉的人們來說,這裏也要安全得多。
另外,他們在成都擴大經營,並由此與其他商人產生了競爭,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當地人的抵制。
在成都有一個廣爲流傳的故事,可以增加我們對新老移民之間緊張關係的瞭解:19世紀80年代,陝西人在成都立腳後,他們想爲同鄉會建造一座會館,但是成都人不喜歡這些暴發的商人,拒絕將土地出售給他們。後來經過多方努力,陝西人買到了一處低凹泥濘的土地。開建前必須用石頭和泥土來填平,但成都人不允許他們從成都就地取土,以此阻礙他們的修建計劃。同鄉會只有號召所有的陝西人從自己的家鄉帶回一袋乾燥的泥土。兩年內窪地即被填平。

現在無從考證這個故事的真假,但故事本身可能誇大了成都人心胸狹窄的特性和他們與陝西人之間的矛盾。不過這個故事的流傳,的確反映了存在於本地人和外來者之間的經常不斷的形式繁多的衝突
清末民初,來成都的移民大幅度增加。一份1917年的報告指出,成都最近增加了二萬餘戶家庭,引起一些人擔心城牆內這有限的地方,如何能容納下這樣巨大的人口。一些人認爲,清政府倒臺後,失業人數增長,這加劇了謀生的困難。成都吸引了來自各個地方的新移民,所以是良莠混雜,一些壞人隱藏在人羣中,可能對社會安全是潛在的威脅。當地報紙報道了一個鄉下人是如何在騾馬市認出一個“面目可憎”漢子,這人是曾經在什邡縣搶劫過他家財物的匪徒。因此,一些地方精英呼籲政府對流動人口給予更多的限制。
成都同中國其它城市一樣,由族羣、籍貫等的差別引發的問題非常普遍。或許城市中鄰裏之間的親密關係強化了“我們”(鄰裏)與“他們”(鄉下人或移民)之間的隔閡。
成都居民不喜歡“陌生人”來改變了他們的日常生活,而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努力在公共空間維持生計和尋找娛樂,這便是在城市中每天都不斷出現的糾紛、衝突、乃至暴力的土壤。
其實,這不是成都的獨特現象,在中國任何一個傳統城市裏,這種衝突都是見慣不驚的,而且實事求是的說,成都還是一個很包容的城市了。直到今天,這個城市仍然是中國的對外來人最感親切的城市之一。
實際上,雖然我們指出了城市中存在的這些問題,但這並不否認在長期歷史過程中成都社會所建立的一種穩定機制。也即是說,即便是在衝突發生時,這種能自我調節的機制也能把衝突限制在比較低的層次上,而很少發生那種不可收拾的大規模騷亂。
原標題:《過去城市中的人與人之間的歧視非常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