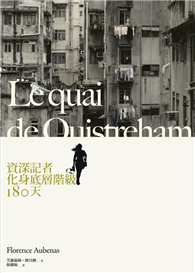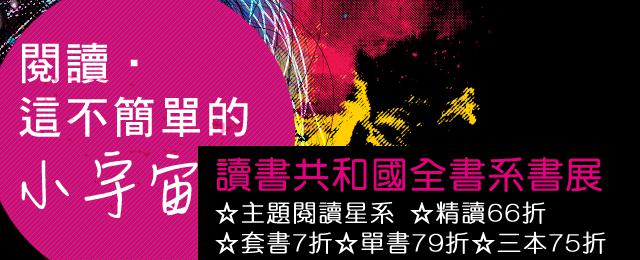【读后笔记】谁是隐形人?《资深记者化身底层阶级180天》
我们每个人的面容都被同样艰难的工作时间表,被这个既痛苦却又嫌不够的工作给折磨得精疲力竭,
空气中有一种超越极限,咄咄逼人的疲惫在微微颤动。
景仰这位战地记者的经验,我读了《Le quai de Quistreham》,中文书名比原本书名耸动多:这名法国战地记者Florence Aubenas不谈结构、不评论政策,写出了那一段隐藏身份当清洁女工的生活,描绘著就业中心的咨询环境、辅导课程、工作伙伴的烦恼。总是会有那样震撼的一句话,周围的清洁从业伙伴告诉她:「当了清洁女工以后妳就会变成隐形人。」
「当清洁人员谈起找工作,大家的说法都一样。最惨的就是这第一次,或者应该说所有的第一次,当你在沉睡中的城市醒来,开车穿过黑夜驶向陌生的地方,因为不知道会遭遇什么,心里七上八下的。
」笔者总是在赶赴新接案的办公场所迷路,不能迟到;迟到后的情况总是惨不忍睹。
其中,谈到有些工会发起失业抗争活动,参加者少,是担心被雇主发现。「开车穿越Quistreham
我猛然惊觉建筑物的墙上竟挂了如此多布条:大学、研究、实验室、工厂医院,数一数整整有十五面,然而却各自躲在自己的故事与自己的抗争之中。」
她笔下的人发言,都是安静苦中作乐的样子,「那个高瘦的人起身离开,在异常蔚蓝的天空下自言自语道:为什么是员工在为工厂哀悼?难过的人应该是老板才对。」
还有一个机会是搭上法国游览的就业列车,到各城镇去找工作,上头会刊载各大厂的招募。「就业中心,也不喜欢民众没有透过她们,就自己跑到现场:万一应征上,对她们的招募统计数据并无帮助。」
前言中Florence在'09年写著:「发生了金融危机,记得吗?以前曾经发生过,很久很久以前,就在去年。金融危机,大伙的话题总离不开这个,但只是不所以然地闲聊,也拿不出解决办法,甚至连眼睛都不知该往哪儿看,在在让人觉得这个世界就要分崩离析了。然而,我们周遭的事务似乎始终待在原处,像是动也没动过。」两年前写下的字对照'11年底此刻,当初救急的世界金融,再度混乱著,我觉得悲观。没有人想要回到无薪假的日子吧!全球青年贫穷化失业指数高,还有那些在外国打工/社会最低阶的人们呢?
目前30岁以下年轻族群(包括我在内)憧憬著去他国打工,做低阶的工作;书中显指出不利的就业条件下,连法国本国人都被歧视,更何况是亚洲人?巴黎念书友人反应说,中国学生在中国餐馆打工一小时5欧元,拥有义大利餐馆专业的服务生朋友,一星期薪水却可以付一个月房租还能买一件大衣。我们或许不论金钱多寡,看到优点是,赚到了异地生活经验,也提升了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但是事实是:每个国家都存在著,青年不愿意做、容易被汰换的工作,原本国家没有人作,而由外国人作,全球人才流动,而全球的青年失业率高。而我们是怎么对外籍工作者的呢?
2007年夏天我踏出校门,'08年金融海啸后'09夏季我曾经换工作,目前工作的主管面试问我:之前两个工作为什么都一年半,这么短的时间?
我答:毕业后大学新鲜人没有经验,是自己预设的出版圈范围内,我就去了,当时的就业市场,平均是五个人抢一分工作、没有挑剔的机会。当然,不细究经手的工作内容多样化跟薪资其中有拿政府22K......种种菜鸟职场乱象,我感谢那些给我机会的主管,让我有了三年经验值,现在才有那么一点「贡献社会的生存感」。前辈老师跟商业杂志上都说:30岁之前不该计较薪水;不靠父母,不窝回家乡,在台北能够付起房租,让生活与心灵俭朴,这几年的确很辛苦。
最后,我回想起巴黎地铁给我的印象之一,地铁途中,一回正对面是欧洲古典小脸正妹,穿著白纱套装高贵优雅,存在淡漠的气质;一回对面是疲惫无表情的油漆工人,连身裤装沾满了花色干去的涂料。城市里并存各种阶层的人,我们都有惊奇眼光。
若妳也希望关于法国的书架上,并不只有「充斥著对巴黎想像的图文书」而已,可以读这一本纪实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