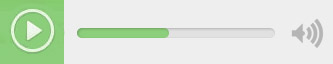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法律適用及舉證責任分配
▽
中國有句俗話,「清官難斷家務事」。勞動人民的智慧總結看起來古樸通俗,細細品味卻又哲理深邃。就如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無論是從立法還是司法層面思考都是一個法律難題。
2018年1月16日,最高法院頒布了《關於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下文簡稱《2018夫妻債務新司解》)。短短四條全文的司法解釋,足以顯現司法機構對夫妻共同債務認定規則予以改進的迫切程度。任何法律規則的頒布離不開社會生活背景,該司法解釋的出臺,可以說是為瞭解決過往《婚姻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中對夫妻共同債務法律推定「一刀切」的「不合時宜」感。但是,該解釋對於後續審判實務的影響以及帶來的適用難度還是讓筆者感到擔憂。實踐中,會不會從一個極端到另外一個極端?本文通過一個假設的案例來揭示這份擔憂的存在,並以此探討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法律適用及舉證責任分配問題。
一、案情設定
2016年6月16日,某甲與某乙登記離婚。
2016年3月,某甲兩次向某丙借款,後陸續償還,但尚欠五萬元人民幣到期未予償還。某丙遂將某甲與某乙夫妻二人訴至法院,且認為借款行為即債務發生在夫妻關係存續期間,要求某甲與某乙承擔共同還款責任。某乙認為,該債務資金系某甲用於賭博,並未用於夫妻共同生活,不能認為是夫妻共同債務。另外一個設定的條件就是,案件審理期間,《2018夫妻債務新司解》已經公佈並施行。
一種觀點認為,應當支持某丙的訴求,主要依據在於貸款額度不大,且發生於夫妻關係存續期間,而某乙雖然提出抗辯,但其對於債務資金系某甲用於賭博、並未用於夫妻共同生活的主張,並未提交證據佐證。
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為,應當駁回某丙的訴求。根據《2018夫妻債務新司解》的新規定,債權人某丙應當對某甲的借款是否用於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或者基於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承擔舉證責任,因為某丙就其主張未能提供證據證明,故應承擔舉證不能後果,涉案借款不屬於夫妻共同債務。
從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在最高法院《2018夫妻債務新司解》頒布實施後,有觀點認為應由債權人舉證證明借款用途,不能證明的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後果。必須正視的現象(問題)是,由於借款用途的直接證據往往都在債務人控制之下,讓債權人證明借款用途並承擔舉證不能的後果,實質上有可能造成絕大多數債務都將被認定為個人債務,而非夫妻共同債務。
二、問題提出及應對方案
在許多討論場合,上述第二種觀點帶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結合上述設例,本文對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法律適用及舉證責任分配問題進行簡要探討,並提出意見和建議。
(一)兩項司法解釋中關於夫妻共同債務認定規則的不同技術思路
1 . 法律推定及不對等舉證原則
2001年頒布的《婚姻法》第41條第一款規定,「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共同償還。」
2003年頒布的最高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下文簡稱《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於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情形的除外。」
從法律解釋理論看,法律規定的立法本意是司法解釋的基礎,司法解釋不能脫離法律的立法本意肆意解釋。《婚姻法》的規定確立了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原則,即是「債務用途決定債務主體」,用於夫妻共同生活的即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金錢作為一般等價物的特性,決定了司法實踐中任何一方證明金錢的精確用途都是一項困難的任務。為此,《婚姻法》解釋二採取了「法律推定」的解釋思路,原則上,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均推定為用於夫妻共同生活,故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除非夫妻一方能夠舉出反證。
《婚姻法》解釋二原則上遵循了《婚姻法》的規定,只是在法律證明路徑方面進行了明確,並非對立法本意的修改。但是,法律推定規則必然導致加重不利方的舉證責任,可謂「不對等舉證」。《婚姻法》解釋二對夫妻一方而言存在明顯不利,客觀上造成了絕大部分夫妻一方名義所負債務均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或許正是由於這樣的結果導致了較大社會不滿,特別是近年來民間非法集資現象嚴重的背景之下,可能讓確實不知情的夫妻一方承擔了巨額債務,對社會、家庭帶來了負面影響。
2 . 查明事實及雙方對等舉證原則
《2018夫妻債務新司解》從根本上放棄了《婚姻法》解釋二採用的法律推定技術思路,除了規定明確有夫妻雙方意思表示當然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外,對於其他情形依然採取以查明事實為目標的「雙方對等舉證」的思路,即以法院為主導,以查明是否用於「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事實為核心目標,原被告雙方舉證證明債務的實際用途。
可以說,《2018夫妻債務新司解》是大陸法「糾問制」訴訟思想的經典展現。
筆者注意到,《2018夫妻債務新司解》無論第2條還是第3條,規定「債權人以屬於夫妻共同債務為由主張權利的」均要以是否用於「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事實為前提。權利主張需要事實主張的支持,一般理論認為事實主張需要權利主張方承擔舉證責任。但是,我們仔細分析《2018夫妻債務新司解》第2條和第3條的表述,司法解釋的本意看來並不是僅僅要求權利主張一方承擔舉證責任,反駁方同樣需要舉證反駁事實的存在,屬於共同舉證法院查明事實的範疇。
《2018夫妻債務新司解》第2條規定,「夫妻一方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債權人以屬於夫妻共同債務為由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第3條規定「夫妻一方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債權人以屬於夫妻共同債務為由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債權人能夠證明該債務用於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或者基於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對上述兩條規定做如下分析:
一是「夫妻共同生活所負」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不同。
《婚姻法》規定,「夫妻共同生活所負」債務均為夫妻共同債務。該規定僅僅限定了用途的性質,未限定用途的「用量」,即只定性不定量,也是說只要用於夫妻共同生活,無論奢侈與否都認為是夫妻共同債務。但是,《2018夫妻債務新司解》既定性也定量,不但要求用於家庭生活,而且必須是「日常生活所需」,超過日常「用量」除非能夠證明「用於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或者基於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否則不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
二是法官應當根據雙方舉證判斷是否用於「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多數人也許認為,是否用於「家庭日常生活需要」這一事實應當由權利主張方債權人舉證證明,但假設此觀點正確的話,那麼第2、3條司法解釋其實可以合併表述為:「夫妻一方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所負的債務均推定為個人債務,但債權人能夠證明該債務用於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或者基於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如果是這樣,那麼該規定與《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的法律推定截然相反。但是《2018夫妻債務新司解》並未如此表述,而是分為兩個條款區別不同情況分別表述。筆者認為,之所以如此表述,其解釋本意是要求對於借款用途問題作為法院應當查明的事實,而不是作為一方當事人的舉證責任。
讓我們回到先前的案例,認識這一問題的區別就在於,是將「借款債務的實際用途」作為裁判者應查明的事實而要求雙方提供證據證明後法院進行判斷認定,還是將其作為債權人單方面的舉證責任,最終認為債權人未能對「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或者基於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進行舉證。
司法實踐中,如果讓「夫妻一方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所負的債務均推定為個人債務」成為現實,與《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相比,顯然是從一個極端到另外一個極端。
(二)法官查明事實理論依據和路徑建議
1 . 法律規則的合理運用
理論上看,「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和「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兩個事實均屬於積極事實,其實質是「借款債務的實際用途」,從證明可行性上說均屬於可以證明的事實。因此,將該事實作為法院應當查明的事實,從而要求雙方舉證證明在理論和實踐上均是可行的。我國在訴訟程序上一直秉承大陸法系糾問式審判思維,且《民事訴訟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護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保證人民法院查明事實,分清是非,正確適用法律,及時審理民事案件…」。因此,將「借款債務的實際用途」作為法院應當查明的事實具有法律原則依據。
也許會有人提出疑問,要求雙方舉證是否違反「誰主張誰舉證」的基本證據規則?
筆者認為,在認定是否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事實問題上,要求雙方舉證並不違反舉證規則,相反具有充足的成文法依據。
《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客觀分析,是否用於「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證據,絕大多數在債務人控制之下,如果單方面要求債權人收集債務人控制的證據,在不適當使用公權力介入的情形下恐怕絕大多數債權人都無法舉證。因此,此時債權人依據《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申請法院調查於法有據。另外,《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94條第二款規定,「涉及國家祕密、商業祕密或者個人隱私的」,屬於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筆者認為,債務人的日常消費、資金用途確實也屬於個人隱私,基於司法解釋的規定,法院也當然有權主動調查收集相關證據。
2 . 生活經驗的合理判斷
也許有人會提出另一個疑問,如果把「借款債務的實際用途」作為法院應當查明的事實,但是最終事實無法查明怎麼辦?
必須看到的是,法律事實並非客觀事實,而是經驗事實,事實的準確度只是蓋然性高低的問題。每個人的生活都會留下痕跡,這些痕跡構成了一個人的生活習慣,當然也包括消費習慣,即使無法準確追蹤借款的實際用途,也可以通過對個人消費習慣的判斷認定是否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舉個例子,一個年收入五百萬的人,每個月消費十萬左右,如果他因臨時周轉出現問題,向他人借款五萬元,作為具有日常生活經驗的人都會認為這是合理的家庭消費借款。但是,如果一個年收入只有三萬的人向他人借款五萬,任何一個具有日常生活經驗的人都不會認為借款會用於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另外,筆者注意到,2018年1月17日人民法院新聞傳媒總社發表的《妥善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 依法平等保護各方當事人合法權益》的文章,其中對於涉及夫妻共同債務糾紛案件中的舉證證明責任如何分配問題,原文答案如下:
「《解釋》前三個條款雖然分別規定了共同意思表示所負的夫妻共同債務、家庭日常生活所負的夫妻共同債務、債權人能夠證明的夫妻共同債務,但從舉證證明責任分配的角度看,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家庭日常生活所負的共同債務;二是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負的共同債務。對於前者,原則上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債權人無需舉證證明;如果舉債人的配偶一方反駁認為不屬於夫妻共同債務的,則由其舉證證明所負債務並非用於家庭日常生活。對於後者,雖然債務形成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和夫妻共同財產制下,但一般情況下並不當然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債權人主張屬於夫妻共同債務的,應當由其根據《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等規定,舉證證明該債務屬於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所負債務,或者所負債務基於夫妻雙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如果債權人不能證明的,則不能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
再結合近期最高法院幾位法官聯合發表的《<關於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該文章認為,「對於《解釋》第二條規定的夫妻一方為家庭日常生活所負的債務,原則上應當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債權人只需要舉證證明債權債務關係存在、債務符合當地一般認為的家庭日常生活範圍即可,不需要舉證證明該債務用於家庭日常生活。如果舉債人的配偶一方反駁認為不屬於夫妻共同債務的,則由其舉證證明所負債務並非用於夫妻共同生活。為家庭日常生活形成債務的舉證證明責任分配,符合婚姻法關於夫妻地位平等和對共同財產有平等處理權的規定,大大減輕了債權人舉證證明責任,有效保護了債權人合法權益。」
從上述官方解答和學術文章看,對於是否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問題並不是完全依賴於單方面債權人「精確」舉證,只要根據一般生活經驗判斷即可,且債務人反駁的也應當提供證據證明。上述觀點從一定程度上認可了是否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問題應當屬於法院查明事實範疇的觀點。
總之,筆者認為,我們不能把《2018夫妻債務新司解》簡單認為是一種個人債務的法律推定,從而一律要求債權人對共同債務的主張進行舉證。法官在審理此類案件時,應當從查明事實出發,要求雙方共同對借款用途進行舉證,並根據舉證結果情況合理判斷借款用途是否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三、《2018夫妻債務新司解》的社會正麵價值
從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司法解釋發展來看,司法實踐必須與社會現實相適應,「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英美法更注重經驗判斷的司法思路值得我們借鑒。
在近年來民間融資爆發性發展的背景下,因為夫妻一方的一時貪婪,讓越來越多的家庭背上了巨額負擔,如果機械按照《婚姻法》解釋二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那將勢必讓絕大多數不知曉實情的夫妻一方背上沉重負擔,既不利於家庭和諧、子女養育,更不利於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2018夫妻債務新司解》能夠從社會實際出發,遵從於《婚姻法》立法本意,合理將查明是否用於「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問題賦予法院承擔,讓原被告雙方對等舉證,共同查清事實,體現了法律追求的平等與公正價值。
最後,筆者想說,婚姻需要雙方的經營管理,夫妻雙方既有相扶相助的義務,更有相互監督的責任,夫妻雙方都需要關注對方的行為舉止,都需要以正確的「三觀」引導、教育、影響對方。
我們不能期待用法律解決一切問題,更不能依賴用法律規制所有人的行為。每個人的心裡都有一個魔鬼,只有理性的牢籠足夠堅固,魅影才只能遊盪於籠中。
丁明,1978年4月生,畢業於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系,現供職於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