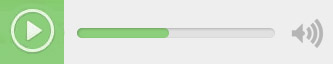阡陌上的清明
讀
春天生長的不只是
綠柳紅桃
還有一輩輩人,以及骨質里
父析子荷的血脈傳承

當柳綠含煙、桃紅宿雨,就清明了。無論作為節日,還是節氣,清明都行走在阡陌上。
少不更事,不知何謂踏春,只喜歡在深綠淺紅里「沾花惹草」,渾身弄得「奼紫嫣紅」。但有一天,我會很老實,衣著整潔地跟著父親,去拜訪一座墳。那座墳里,住著爺爺。那天,是清明節。父親不說話,給墳添土、燒紙錢。以致很多年,我都以為爺爺是父親種在地下的莊稼,也會像柳樹抽枝吐翠,或者像桃樹開花結果。
在鄉間,柳樹是村莊的鬍鬚,我們則是頑劣的理髮師。當「寒食東風御柳斜」,我們就爬上柳樹,折柳枝,編帽子,制柳笛。「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把春風趕得落紅滿地。柳樹則像寬容的父親,微笑看著,任憑我們折騰。
年歲漸長,慢慢發現,父親也像柳樹。兒子是父親的影子,父親是柳樹的影子。那些柳樹,我爬過,折過柳枝;父親的脖子,我也爬過,拔過鬍鬚。後來,柳樹彎了脖子,父親彎了腰。再後來,時間像一塊結石,堵在胸口,讓我恐慌不已。
那個春天的喪事,讓我參透柳樹。二爺睡在棺材裡,二叔扛著柳幡,在前面引路,後面跟著一群人,手裡都拿著柳枝。恍惚間,二爺變成一棵柳樹,那些哭喊的後輩,都是他春風裡的枝椏。他曾把二叔扛在肩上,現在二叔扛著他,把他當成一粒種子,種進地里。
兒子的成長,總背對著父親,影子卻像根,扎在父親肥沃的時光里。母親是那滿院的桃花吧?絢爛、甜蜜了我最初的夢。「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父親不懂這些,他還是在院里種滿桃樹。母親體質弱,桃樹可以辟邪;我嘴饞,桃子可以解饞。
如今,父親種的桃樹都老了,他卻隨村裡的年輕人,南下打工。臨行時,他反覆叮囑,清明別忘了給爺爺上墳。為了我的家,父親可以背井離鄉,但他忘不了爺爺的墳。在父親心裡,那座墳冢就是爺爺的家。冢和家,只隔著子孫那一杴新土、一沓火紙。
清明回家,正桃紅柳綠。又一輩的頑童,玩著我兒時的遊戲,「興逐亂紅穿柳巷」。時間猶如桃樹下的鞦韆,盪過來,盪過去,花相似,人不同。「陰陽無途通音問,清明尋路且上墳」。父親不在,這條路該我尋了。我學著父親,給爺爺燒錢紙,修「房子」。
「墳頭掊土新疊舊,墳前草木枯又青;音容應在此地下,湮沒黃塵多少春?」這是爺爺出給父親的算術題,我算不出,父親能。修完「房頂」,還要給墳戴頂「帽子」——做個墳頭。冢上加一點,就是家了。清明過後,就是夏天,那麼熱的天,不戴頂帽子,爺爺會中暑……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春煙。」大人上墳,孩子攀柳折花,笑聲像飽滿的芽尖,啄破歲月,在春風裡抽枝吐翠。「萬物生長此時,皆清潔而明凈。故謂之清明。」春天生長的不只是綠柳紅桃,還有一輩輩人,以及骨質里父析子荷的血脈傳承。
小苑
葛亞夫,男,八零後,筆名洛水等,省作協會員。支過邊,辦過報,兼過編輯、記者。現耕教於莊子故里。各類作品散見於《詩歌月刊》《小小說選刊》《散文世界》《讀者》《意林》《人民日報》等報刊雜誌。
【謝謝關注,多多交流】
你的讚賞是我堅持原創的動力
讚賞共 0 人讚賞推薦閱讀: